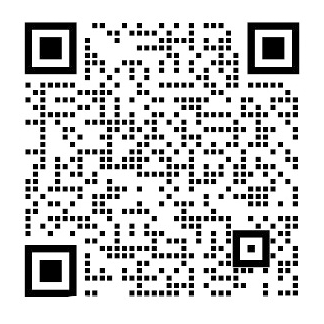游戏和游戏性,幼儿教育的基本特征
原文作者 Elly Singer 单位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发展心理学系
摘要:本文认为游戏和嬉戏是幼儿教育的基本特征,但游戏课程可能存在严重缺陷。以荷兰历史学家约翰·惠辛加(Johan Huizinga)的游戏理论为起点,他是一位激进的批评者,他对游戏的教育益处进行了激进的批评。在惠辛加看来,游戏的本质特征是愉悦,游戏给人一种自由的感觉。当过度关注游戏的教育益处时,游戏最本质的特征——孩子们的快乐就消失了。在游戏中,儿童和成人共同构建了一个共享的世界,他们能够根据现实调整自己的经验。最近对教养者-婴儿沟通、神经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的研究与惠辛加的理论是一致的。没有游戏,在复杂的社会世界中适应和生存将是困难的。游戏有助于克服教养者与孩子关系中的权力差异,游戏是共享快乐和创造力的资源。
关键词:游戏理论;游戏课程;日托;师生交流;幼儿
介绍
“让我的玩耍成为我的学习,我的学习成为我的玩耍”是众所周知的一种对游戏进步的表达。自从启蒙运动以来,游戏就与道德、社会、情感和认知的学习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福禄贝尔、蒙台梭利、施泰纳和马拉古齐等西方幼儿教育的创始人都专注于积极游戏和学习的孩子(Singer 1992)。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许多发展研究都试图证明游戏的教育益处。事实上,在许多研究中——尽管不是全部——都发现了这种关系,例如爱游戏的母亲和其幼儿后来社交技能之间,或者是在假装游戏和后来的抽象思维之间(Sutton-Smith 1997)。与以教学和知识传播为目的的教师课程不同,“游戏课程”过去和现在都被视为以儿童为中心且适合发展的课程。但游戏课程也有其缺点。根据 Sutton-Smith (1997) 的说法,将游戏视为进步的信念和刺激发展的王道在教育话语中变得如此占主导地位,以至于我们倾向于忘记玩耍的孩子本身。儿童的游戏理念通常集中在“玩乐、户外活动、与朋友在一起、自由选择”(49)。教师往往表现得过于“教师化”,并滥用儿童游戏来实现自己的教育目标,从而破坏了儿童的乐趣(Pramling Samuelsson 和 Carlsson 2008)。
荷兰历史学家约翰·惠辛加(Johan Huizinga)是最早也是最激进的批评者之一,他认为游戏的社会和教育利益受到过多关注,他声称游戏的本质迷失在他所谓的“功能主义游戏方法”中。在1938 年首次出版的《Homo luden》一书中,他写道:“首先,所有游戏都是一项自愿活动[hellip;hellip;] 儿童和动物之所以游戏游戏,是因为他们喜欢玩耍,而这正是他们的自由所在。”(8)
惠辛加将游戏分析为一种自由而有意义的活动,与实际生活的义务相分离。我将从惠辛加理论的一些核心论点开始,然后将他的见解应用到最近的幼儿教育游戏理论中。在惠辛加之后,我认为游戏本身就是幼儿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将我的论点集中在非常幼小的人——四岁以下的孩子身上——并从对日托中心和游戏小组的研究和观察中得出我的说明性例子。 惠辛加对游戏的反教育态度表明,无论是儿童还是教师,游戏和嬉戏都必须被视为幼儿教育和照料的基本特征。
不可还原的游戏体验
惠辛加的哲学出发点是游戏对玩家来说是有意义的这一观点。“所有游戏都意味着某种东西”(1)。玩游戏的基本动机是它提供的体验。惠辛加举了两只小狗参与打斗的例子。“他们遵守规则,你不能咬你兄弟的耳朵,也不能用力咬。他们假装生气。最重要的是——在所有这些行为中,他们显然体验到了巨大的乐趣和享受”(1)。
人类也为了主观体验而玩耍。根据惠辛加的说法,这些体验只能通过对兴奋、紧张、释放、不确定、团结、惊喜、节奏、风险、平衡等感觉的定性描述来捕捉。他批评心理学和生物学理论,这些理论旨在根据游戏的假定功能和生物学或社会效益来解释游戏的性质和存在。他指出了这些理论中引用的功能和益处的巨大差异。心理学家声称,孩子们玩耍是为了释放过剩的能量,为生活的需求做准备,锻炼运动技能,培养自我控制和挫折承受能力,或者实现愿望。在这种功能的多样性中,游戏在学习和发展中最基本的功能就丧失了。
在这种强度、这种专注、这种令人发狂的力量中,蕴藏着游戏的本质和原始品质。我们的理性头脑告诉我们,大自然本来可以很容易地赋予她的孩子所有有用的功能,如释放过剩的能量、在劳累后放松、训练满足生活的需求、补偿未实现的渴望等等。纯机械练习和反应的形式。但不,她给我们带来了游戏,充满了紧张、欢乐和乐趣。(惠辛加 1955, 3)
所有这些功能主义的游戏方法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假设游戏必须服务于其他不是游戏的东西。 惠辛加断言,一个人可以完全接受所有关于游戏益处的理论,而无需抓住游戏的本质——因为“乐趣元素才是游戏本质的特征。我们必须处理一个绝对主要的生命类别。孩子们不玩是因为一些比玩本身更有价值的好处,成年人也一样。
节奏、规则和魔法圈
惠辛加对游戏的主观体验的强调可能表明他是从个人主义假设开始的。但在他的作品中,“体验”并不是指一个孤立个体的内在状态。游戏假定与直接的社会和物质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孩子与朋友或成人一起玩耍,并与他或她的环境中的物体玩耍。相对于其他人和周围环境,玩耍的孩子创造了一个不同于“正常世界”的游戏世界,其中节奏、规则和结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教养者与婴儿互动的细致分析表明,例如,双方通过相互模仿、眼神交流、轮流、重复、变化和即兴发出的声音,共同创造了一个游戏世界(Trevarthen 2011;DeZutter 2007)游戏中也存在与物理环境的重复结构。例如,婴儿掉落物体时会听到扑通声,然后用疑问和热情的眼神看着教养者,教养者必须捡起并归还物体,以便婴儿可以再次掉落。教养者和婴儿一起创造一种节奏或模式,他们会通过改变以保持兴奋。这些最初的滑稽、非语言交流形式类似于一起跳舞或制作音乐(Malloch 和 Trevarthen 2009;Stern 2000)。共享的游戏世界通常具有“魔法圈”的特征。例如,想象一位助教给孩子们朗读故事:在聆听的同时,他们被传送到另一个世界。或者想想那些全神贯注于玩汽车、玩偶或扮演老虎或猫咪的孩子。
通常,成年人通过游戏规则和时空划分明确区分“游戏世界”和“现实世界”。在剧院里,这是一个假装的问题。由于球员必须遵守的规则,足球或国际象棋比赛是“对战”的形式。足球或国际象棋比赛期间的比赛由比赛规则划定。对于年幼的孩子,游戏的规则和结构仍然简单而松散,在游戏过程中很容易改变。幼儿的游戏往往具有一系列重复动作的特点。一个两岁的孩子用脚在沙发上打鼓可以发展成一个有四五个孩子的齐声击鼓(Loslash;kken 2000)。孩子们可以让这些重复的一系列动作成长为更全面的仪式。例如,餐桌上的午餐以唱歌、拍手和最后鼓掌结束(Corsaro 2010)。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全世界孩子都喜欢的躲猫猫游戏。与他们的教养者或其他孩子一起。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建构主义者谈到了“共建”(Valsener and Vos 1996)。通过一系列动作的重复和变化,幼儿与看护人和其他孩子“共同构建”一个共享的游戏现实。
自由调整体验
游戏不是“正常”或“实际”的生活;在游戏中,我们创造了一个临时的活动范围,一个不同于“正常”的游戏世界。但“只是玩”的意识并不意味着儿童和成人不能认真地沉浸在游戏中,迷失自己。根据惠辛加的说法,在每一个严肃的文化机构中都可以找到游戏元素——法律、经济、宗教甚至军队(Huizinga 1955)。在所有这些制度中,仪式都发挥了作用,即相关的行为模式赋予核心价值或社会关系以形式。仪式表达了核心价值,能够使“真实”或代表无法客观证明的真理。例如,法官穿着长袍,这是一种仪式服装,用来表示和划定法律的“游戏世界”。彼得森先生不再是平常的彼得森先生,而是“法官”。神圣的仪式通常具有一种假装游戏的结构,在其中体现了宗教团体的经验,即神圣真理(De Botton 2012)。例如,基督教的圣餐仪式,与基督的身体和血液的联系;根据天主教和东正教神学,在这个仪式中,酒和面包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液。人们通过仪式创造一种公共现实、一种文化;他们创造了一个揭示“真相”的神奇世界;并在此过程中表达了他们作为人的自由。
儿童游戏中也经常出现严肃性,尤其是当孩子们全神贯注于他们的游戏时。如果一个3岁的孩子全神贯注地玩洋娃娃或玩火车,但被另一个孩子打断时,他或她的反应往往是暴力的。孩子很生气。他或她的游戏世界的魔力被打破了。孩子们表演严肃的经历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历(Kalliala 2006;Rogers amp; Evans 2008)。入院后,孩子们经常会在医生面前玩耍。 “母婴”是一个深受喜爱的主题,在其中展现了他或她对爱、依赖和力量的最基本体验。通过假装游戏,孩子们从部分压倒他们的经历中创造出他们自己的主观游戏世界。他们将体验变成了自己的体验——或者用惠辛加的话来说,孩子们在游戏中创造了摆脱不可避免的自由的自由。
在惠辛加的现象学分析中,游戏反对功利主义的、物质上重要的、由承认社会和自然规律要求或产生的工作。游戏突破了支配“正常”生活的法治。根据现代博弈论专家Rodriguez (2006) 的说法,这是惠辛加博弈论的基石。
逻辑思维和游戏的基本目标不同。按照传统的解释,逻辑的重点是建立正确推理的明确标准。相比之下,游戏的基本目标是调节玩家的体验(4)。
在游戏中,我们可以暂时摆脱这种法治和“正常”生活的义务。游戏给人一种自由的感觉。也许这就是让游戏令人兴奋的原因:在游戏中改变我们对现实的体验的自由。事实上,这是高度多样化的游戏形式的共同点。一群两岁的孩子围着桌子笑着尖叫着,在他们的游戏中忘记了他们跌倒再爬起来伤害自己,因为他们还不能正常跑步。一个三岁的孩子可以享受“在医生那里玩耍”的乐趣,而不必担心医生可能真的会伤害他或她。当助教朗读小熊失去母亲的故事时,孩子们可以愉快地进入故事,而不会感到任何真正的失去的恐惧。
幼儿游戏与严肃生活之间的细微分界线
游戏和“正常”生活之间总是存在紧张关系。成年玩家意识到“游戏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的界限。游戏有开始和结束,并以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和规则为标志:例如,想想竞技自行车或剧院的游戏规则。但这些规则是可以被打破的——有时甚至作为游戏(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构的?)有时打破规则会唤起一种背叛感,例如国际自行车运动中的兴奋剂事件和足球中巨额资金的作用。运动仍然是运动还是纯粹是钱的问题?但在游戏世界的划分方面,成人和幼儿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两三岁的孩子直观地知道“为了好玩”和“为了真实”之间的区别。他们扮演“狗”或“妈妈”,在游戏期间他们完全是这样。当他们停止玩耍时,他们非常清楚自己不是狗或母亲。但是游戏和“真实”之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和流动的。从“真实”到“游戏”的流畅过渡,反之亦然,这是一种经常与幼儿观察到的现象。幼儿的幽默和笑话常常基于这种转变(Loizou 2005;Singer amp; De Haan 2007a)。有时冲突会以这种方式解决。举个例子:
三个三岁的孩子一起玩。有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他们喋喋不休地在操场上走来走去。 一个女孩突然对男孩说:“走开”,然后把他推开。男孩看起来很惊讶,呆在原地。“走”女孩又说了一遍。“不,”男孩说。“不,”女孩模仿他说。“不”,男孩重复道,这次声音更大了。不到一分钟,一个“不”的游戏就形成了,一种唱歌的游戏,第二个女孩也加入其中。孩子们显然喜欢轮流喊“不”:冲突变成了游戏。(观察 ES)
游戏是文化的源泉之一
惠辛加并不认为游戏是社会生活和文化的一个方面,与其他方面并驾齐驱。他的目标更加雄心勃勃。他认为游戏是文化的源泉之一。文化的发展得益于生物——动物和人类——通过自由创造新的游戏——“现实”来改变他们的体验的能力。文化的核心是由游戏、欢乐的即兴创作、笑话和幽默、竞争和竞赛的元素构成的,使图像成为现实。没有游戏,生活就会从文化中消失。
总结一下,可以说游戏可以具有以下特征:
bull; 游戏本身就有价值;游戏带来快乐
bull; 游戏通过节奏、规则和结构进行绑定
bull; 游戏提供了改变体验的自由
bull; 游戏受限于流动的边界,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规则
bull; 游戏是文化的源泉之一
有趣的互动和叙事的音乐性
惠辛加所提出的“人类本质上是游戏”的理论(Homo ludens)在关键点上与婴儿和父母之间玩耍交流的理论以及神经生理学理论相吻合。自1960年代以来,研究人员一直从事母婴互动的微观分析(Blurton Jones 1972;Connolly 和 Bruner 1974;Schaffer 1977;Stern 2002;Trevarthen 和 Aitken 2001)。这些研究非常具有说服性,婴儿从一开始就是与父母或教养者互动的积极参与者。新生婴儿可以警觉、动作协调、有自我意识并能够模仿他人的表情。交流具有游戏的特点。
观察到新生婴儿会“引起”刚被模仿的细心父母的确认(Nagy 和 Molnaacute;r,2004 年)。在亲子关系中,眼球运动、面部表情、发声和手臂和腿的运动成为相互愉悦的互动的一部分。在1970年代,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玛丽贝特森在一个9周大的婴儿身上分析了这些现象。她将这种互动称为“原始对话”,并将其描述为“一种令人愉悦的、仪式化的礼貌”(1979, 65)。她坚信原始对话是她从人类学研究中了解到的“仪式治疗实践”的来源。她是最早指出儿童早期仪式和游戏之间的关系的人之一,以及在惠辛加的作品中分析的文化层面的仪式和游戏之间的关系的人之一。
最近对婴儿和父母互动的研究表明,他们的结构类似于音乐和舞蹈,并且具有俏皮的叙事品质。面部和身体的发声和动作遵循节奏;他们会及时跟随声音和运动的模式。Stern等研究人员撰写了“情感叙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Play and playfulness, basic features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Elly Singer
Abstrac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play and playfulness are basic feature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but that play curricula can have serious drawbacks. The starting point is the play theory of the Dutch historian Johan Huizinga, a radical critic of the focus on the educational benefits of play. According to Huizinga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play is pleasure, and play gives a sense of freedom. When the focus on the educational benefits of play becomes too dominant, the most essential feature of play is lost: childrens pleasure. In play children and adults co-construct a shared world, and they are able to modulate their experiences with reality. Recent studies of caregiver–infant communication, neuropsychology a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re in line with Huizingas theory. Without play, adapting to and surviving in a complex social world would be difficult. Play helps to overcome differences in power in the caregiver–child relationship, and play is a resource of shared pleasure and creativity.
Keywords: play theory;play curricula;daycare;teacher-child communication;very young children
Introduction
Let my playing be my learning, and my learning be my playing is a well-known expression of the belief in play as progress. Ever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play has been associated with moral, social,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Founding parents of Wester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such as Froebel, Montessori, Steiner and Malaguzzi have focused on the active playing and learning child (Singer 1992).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many developmental studies have attempted to demonstrate the educational benefits of play; and indeed in many studies – though not all – such relations were found, e.g. between playful mother–infant and later social skills, or between pretend play and later abstract thinking (Sutton-Smith 1997). Unlike the teacher-based curricula aimed at instructio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lsquo;play curricularsquo; were, and are, seen as child-centred and developmentally appropriate. But play curricula also have their drawbacks. According to Sutton-Smith (1997), the belief in play as progress and the royal road to stimulating development has become so dominant in the educational discourse that we tend to forget the playing child itself. Childrens ideas of play generally centre lsquo;on having fun, being outdoors, being with friends, choosing freelyrsquo; (49). Teachers tend to behave too lsquo;teacherlyrsquo; and misuse childrens play for their own educational goals, thus spoiling childrens fun (Pramling Samuelsson and Carlsson 2008).
Dutch historian Johan Huizinga was among the first and most radical critics of the focus on the social and educational benefits of play, claiming that the essence of play gets lost in what he called the lsquo;functionalist approach of playrsquo;. In Homo luden, first published in 1938 and still acknowledged as a groundbreaking study for modern theories on play, he writes:
First and foremost, all play is a voluntary activity [hellip;] Child and animal play because they enjoy playing, and therein precisely lies their freedom. (8)
Huizinga analysed play as a free and meaningful activity, segregated from the obligations of practical life. I will start with some of the core arguments of Huizingas theory, then apply his insights to recent theories of play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Following Huizinga, I will argue that play is an essential aspec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its own right. I focus my argument on the very young – the under-four-year-olds – and draw my illustrative examples from studies of, and observations in, daycare centres and playgroups. Huizingas anti-educational approach to play makes clear that play and playfulness in both children and teachers have to be considered as basic feature of early childhood and care.
The irreducible experience of play
The philosophical starting point of Huizinga is the observation that playing makes sense to the player. lsquo;All play means somethingrsquo; (1). The basic motive to play is the experience that it affords. Huizinga gives the example of two puppies involved in play-fighting. lsquo;They keep to the rule that you shall not bite, or not bite hard, your brothers ear. They pretend to get angry. And what is most important – in all these doings they plainly experience tremendous fun and enjoymentrsquo; (1).
Humans also play for the sake of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According to Huizinga these experiences can only be captured in qualitative descriptions of feelings like excitement, tension, release, uncertainty, togetherness, surprise, rhythm, risk, balance. He criticises psychological and biological theories that aim to explain the nature and existence of play in terms of its presumed function and biological or social benefits. He points to the enormous diversity in functions and benefits cited in these theories. Psychologists claim that children play to discharge superabundant energy, to prepare for the demands of life, to exercise motor skills, to develop self-control and frustration tolerance, or for wish fulfilment. In this diversity of functions the most essential function of play in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is lost.
In this intensity, this absorption, this power of maddening, lies the very essence, the primordial quality of play. Nature, so our reasoning mind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594635],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以上是毕业论文外文翻译,课题毕业论文、任务书、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