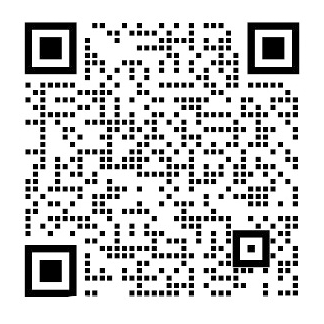Troublesome reproduction: surrogacy under scrutiny
原文作者 Ingvill Stuvoslash;y
单位Norweg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摘要:要近年来,跨国商业代孕安排的出现促使人们考虑,如何以及是否可能构建一种制度,要求去保护无子女夫妇和单身人群的生殖权利,他们中的许多人历史上一直被排除在生殖有效范围外,不享有生殖的权利和福利。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对于讨论如何解决这一挑战的一个富有成效的起点是研究代孕的概念化方式 。因此,我研究了学者们是如何质疑代孕的,询问对这种生殖现象所涉及的人的不同概念是如何导致不同类型的代孕“问题”的。我描述了关 于代孕的三种不同的概念化。首先,代孕作为一种养育父母的方式,由于生殖与消费的融合而困扰着学者们,从而使生殖成为一个经济资源的问题。其次,当代孕被概念化为制造婴儿时,出现的问题与代孕如何将婴儿和身体变成商品有关。第三,代孕被理解为一种涉及妇女怀孕和分娩的现象,这引起了人们对剥削问题的关注。这些不同的麻烦表述指出了文献中的紧张关系,同时也提醒人们代孕混入买卖儿童事;这一发现为新的生殖正义形式提供了机会。这使我提出重新思考“生殖援助”的概念,主张从替代和交易转向关系的存在。
关键词:代孕;代孕福利;女权主义问题;生殖争议;辅助生殖
在这篇文章中,我研究了在学术文献中如何理解代孕,以及不同的概念如何看待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以及不同类型的麻烦。这种检索的目的是促进一场关于如何配置代孕等新的生殖机会,以避免再现社会不平等和支配地位(cf。Luna和Luker,2013)。重视代孕的问题,因为他们在文学中是重要的意识,到这个生殖现象和组织的方式“我们”——作为女权主义者、学者、活动家或同胞——应该不高兴,回忆艾哈迈德的命题,我开始这篇文章。在整篇文章中,我展示了不同的问题焦点:商品化和市场化;开发和分层;生殖选择与消费者选择的融合,选择更多地成为一种需求,对个人要比从国家控制中解放出来。这些不同的问题焦点引起了 代孕不同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的部分原因与不同的代孕模式的存在有关。代孕的大部分麻烦归因于它的商业模式——当代孕同时是商业的和跨国的时,麻烦就会加剧。然而, 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商业化。性别化的(生殖)劳动、自我牺牲和情感管理的概念和种族化的概念,以及“选择”的意识形态配置,也是问题的一部分,使得代孕的利他模式不一定需要避免麻烦和不快乐(cf。鲁德拉帕,2017)。
这种紧张关系也可以被解读为反映了女权主义理论化的历史和政治。汤普森认为,女权主义理论和艺术,包括代孕,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生殖技术已经执行完美的女权主义文本”,结合“经济、技术、个人、法律和政治元素的阶段和冲突的女权主义”(汤普森,2005:56)。激进女权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学者和酷儿女权主义者的不同理论方法为代孕和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观点。因此,代孕不同位于支配、异性恋、资本主义劳动剥削和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的父权结构中。因此,代孕的问题根据当前的社会秩序取决于理论的不同。
亚索米多少不同的阅读这种紧张关系是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是否强调“新”——代孕挑战当前社会秩序——或“旧”,代孕的劳动力分布例证了众所周知的模式的性别、种族、阶级和国家。我自己的出发点是代孕在挪威是新的;同时,这是挪威语的一个新词,指了挪威渴望成为父母的新的生育机会和实践。我对挪威语变化的兴趣在于,它反映了我们对“代孕”观念的变化。在这方面,代孕文献中所提出的不同问题可能会提醒人们,代孕既不是一回事,也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人们(参见里格斯和Due,2013)。在我看来,这一提醒表明了将代孕概念化为一个问题的缺点,仅涉及渴望成为父母、婴儿或代孕母亲。
值得注意的是,把不同的问题放在一起,也可以提醒人们,代孕既不是仅仅违反社会秩序,也不是仅仅与之前的情况相同(cf。斯特拉瑟恩,1995年;汤普森,2005年)。在新旧之间的空间中,也可能有一个替代存在的方式(cf。Ahmed,2010年)和一个不断扩大的可能性领域(cf。巴特勒,2006)。更重要的是,这可能还有另一种思维方式来配置代孕和当代生殖,从而允许新形式的生殖正义。生殖正义,正如我在这里使用的,指的是来自“一场旨在正义的运动”(Luna和Luker,2013:327),同时提出了不拥有和拥有的权利。庚重要的是,生殖正义作为一个框架鼓励“不仅关注选择,而且鼓励关注不同社区之间普遍存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不平等,这些不平等影响了个人获得良好生活的能力”(Rudrappa,2015:182)。此外,生殖正义可以被解读为呼吁分析不同群体之间的生殖和福祉,而不是作为不同的问题(cf。Luna和Luker,2013:345)。这一呼吁指出了将代孕概念化为一个问题的缺点,这个问题仅仅涉及想要成为父母、婴儿或代孕母亲。在回顾了代孕的不同概念,以及每一种概念如何看待不同的人和问题之后,在本文中,我想强调现在代孕需要以一种危及关系的方式概念化 。因此,作为最后的反思,我将通过关注代孕环境中的援助的概念,简要阐述思考和配置生殖关系的替代方法。这样做,我的目标是促进索菲·刘易斯在她2018年关于国际团结、生殖正义和代。孕的文章中发起的对话。
代孕作为一种辅助生殖类型,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第三方复制”(布莱斯和兰道,2004)或“合作复制”(汤普森,2005)。这些定义提请人们注意代孕是一种生殖安排,被理解为不同的人之间的协议,以创造新的人:孩子。这一安排包括想要成为父母的女性,也包括“生父母”(或父母)(特曼,2010)、“帮助”(因霍恩,2010)或“支持”(Vora,2015)的女性,或作为想要成为父母的“替代品”(斯特拉斯恩,1998)或“补充”(巴拉德瓦吉,2012)。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我将这些女性称为“代孕母亲 ”(Stuvoslash;y,2018b)3;这是一种语言结构,我试图捕捉到一种关于这些妇女与家庭、父母和儿童的关系的模糊感。在思考这些妇女提供的援助时,找到一种方法来思考家庭的亲密层面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结构层面似乎很重要。也就是说,找到一种思考生殖关系的方法。一种方法是通过类比资本主义中妇女和生殖的角色来思考这些帮助妇女在代孕安排中的角色。类似的女权主义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妇女和生殖生产在历史上构成了资本主义统治下生产的“背景条件”(弗雷泽,2014;萨森,2000)。相应地,生殖助理员可以被视为构成了非自愿无子女的夫妇和单身人士的家庭制作项目的“背景条件”。比如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前景是如何依赖于“非经济”的背景条件的9弗雷泽,2014:)灵感来自德里达(2016年,orig。1974年)关于海德格尔式的分娩狂喜观念的详细阐述,我省略了“母亲”,因为“代孕母亲”一词是不准确的,并且对它所传达的关于生殖分娩的性别观念有潜在的问题(Pande,2014)。然而,由于“代孕者”一词——或其他常见的替代品,如“妊娠携带者”——并没有更准确或政治责任,“母亲”一词似乎是必要的,因此仍然清晰可见。 这个家庭依赖于一个(构成的)局外人:抚养并生下家庭孩子(伦)的女人。在我看来,一个挑战是找到方法来承认那些帮助他人的人的贡献,而不是“背景条件”,这样“真实”父母的父母才能被合法承认。接受辅助生殖的可能性需要辅助和辅助者可见,而不是降级为“隐藏的住所”。MarxinFraser,2014)。我想在这里建议的是寻找方法,以新的方式来思考这种帮助。我们的雄心可能是从替代和补充意义上的“替代”概念转向更有关系的存在,从而扩大我们的家庭观念,包括对人的重新分类(Lewis,2018:222)。这将更充分地说明如何培养孩子的。汤普森,2005);努力包括超过传统的两个亲生父母。
我认为,代孕的关系可以抵消代孕的问题,比如商品化和剥削,因为它意味着市场交换之外的互惠。因此,它允许坚持将那些提供生殖援助的人视为“完整的人类”(Rudrappa,2015:186),而不要求他们提供劳动作为礼物。这不是一个没有下次的命题,它可以承诺一种不同类型的幸福,而不是一种似乎严重依赖现有社会等级制度的延续以及权力和金钱的不平等分配的幸福。
外文文献出处:Reproductive BioMedicine and Society Online (2018) 7, 33–43
附外文文献原文
understood within the scholarly literature, and how differentconceptualizations bring into view different stakeholders, as well as different types of trouble. The purpose of such anexamination has been to contribute to a conversation on how
new reproductive opportunities such as surrogacy can be configured in ways that avoid reproducing social inequalities and dominance (cf. Luna and Luker, 2013).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troubles of surrogacy as they are posed in the literature is of importance to gain awareness of what there is about this reproductive phenomenon and the ways it is organized thatlsquo;wersquo; – as feminists, scholars, activists or fellow living beings – should be unhappy about, to recall Ahmeds proposition with which I started this article.
Throughout the article, I have displayed different formulations of trouble: commodification and marketization; exploit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and a conflation of reproductive choice with consumer choice, with choice emerging more as a demand on the individual than a liberation from state control. These different formulations of trouble give notice of tensions between different conceptualizations of surrogacy. Part of this tension relates to the existence of different models of surrogacy. Much of the trouble of surrogacy is ascribed to its commercial model – and the trouble is exacerbated when surrogacy is both commercial and transnational. The trouble is not exclusively about commercialization, however. Gendered and racialized notions of (reproductive) labour, self-sacrifice and emotion management, as well as ideological configurations of lsquo;choicersquo;, are also part of the trouble, making the altruistic model of surrogacy not necessarily what it takes to avoid trouble and unhappiness (cf. Rudrappa, 2017).
The tensions may also be read as reflecting a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feminist theorizing. Thompson has argued that feminist theorizing and ART, including surrogacy, have walked hand in hand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as lsquo;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have been performed as the perfect feminist textrsquo;, combining lsquo;the economic, technical, rhetorical, personal, leg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hrough which phases and conflicts of recent feminism have been articulatedrsquo; (Thompson, 2005: 56). The diff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英语原文共 11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596964],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以上是毕业论文外文翻译,课题毕业论文、任务书、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