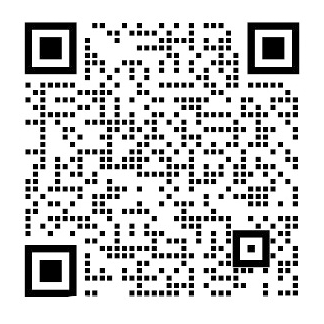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Labor Re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the Clean Air Act
W. Reed Walker
December 8, 2010
Preliminary and incomplete.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newly available data on plant level regulatory status linked to the Census Longitudinal Business Database (LBD) to measure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county leve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on plant and sector employment levels. Estimates from a variety of specifications suggest a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changes in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stringency and both employment growth and levels in the affected sectors. The preferred estimates suggest that changes in county level regulatory status due to the Clean Air Act Amendments of 1990 reduced the size of the regulated sector by as much as 15 percent in the 10 years following the changes.
Walker: Columbi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420 West 118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27, rw2157@columbia.edu. I thank Janet Currie, Lucas Davis, Wolfram Schlenker, and Till von Wachter for helpful discussions and comments. Any opinions and conclusions expressed herein are those of the author(s)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e views of the U.S. Census Bureau. All results have been reviewed to ensure that no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is disclos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limiting emissions of harmful ambient air pollution are designed with health benefits in mind. Associated with these benefits are the costs of abating pollution.The Pollution Abatement Costs and Expenditure Survey suggests that regulations pertaining to the Clean Air Act in the United States account for almost $5 billion in capital expenditures and $20 billion in annual operating costs with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lone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2008). As a result, manufacturers often argue that these regulations place plants and industries at a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forcing plants to downsize or close. Implicit in this argument is tha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lead to job loss associated with industry wide reductions in output.
Accordingly, various papers have looked at the implication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or regulated industries, generally finding negative effects of regulations on industry employment (Vernon Henderson 1996, Michael Greenstone 2002). However, regulation typically affects the distribution of employment among industries rather than the economy wide employment level (Kenneth Arrow, Maureen Cropper, George Eads, Robert Hahn, Lester Lave, Richard Noll, Paul Portney, Milton Russell, Richard Schmalensee, Kerry Smith amp; Robert Stavins 1996). As a result, the appropriate measure of regulatory costs to the workforce should not be characterized by jobs lost but by any transitional costs associated with reallocating production or workers (Arrow et al. 1996, Greenstone 2002). To the extent that workers simply transition from one employer to the next without losses pertaining to job specific human capital or unemployment, it is not clear that job loss should be a net cost when evaluating regulations. Even though this fact has been pointed out in numerous papers, little to no work has attempted to understand the magnitudes of these frictions in the contex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 goal of this paper is to begin to understand the degree to which changes in regulatory stringency over time from the Clean Air Act (CAA) have contributed to costly job transitions to the affected workforce. Recent work linking plant level job ow statistics to worker level job turnover surveys has found a strong link between plant level job destruction and involuntary worker level job loss (Steven Davis, Jason Faberman amp; John Haltiwanger 2006), where layoffs are likely to result both in significant non-employment spells and earnings losses (see Till Von Wachter, Jae Song amp; Joyce Manchester (2009) for recent evidence). Thus, the margins of adjustment at the rm level have important distributional implications for the affected work-
force. To the extent that firms adjust labor demand by increasing ring rates (job destruction), decreasing hiring rates (job attrition), reducing plant entry rates, or increasing plant exit rates, workers will be more or less affected in terms of job loss and/or losses pertaining to job specific human capital.
This is the first paper to decompose net changes in employment due to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into job ow components, offering new insight as to the distributional impacts of regulation on the affected workforce. In doing so, I draw upon the most detailed and comprehensive data available on plant level regulatory status over time; a confidential establishment-level, longitudinal databas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 that I am able to link to a plant level regulatory database from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I can explicitly observe plant level regulatory status over time and observe how these plants respond to 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changes. Previous work inferring regulatory stringency is based on 2- and 4-digit, nationwide industry classifications.
A further contribution is that no research has evaluated the most recent amendments and changes to the CAA on employment. Previous work estimating the costs of the CAA focuses on earlier time horizons, when pollution levels were much higher and technological constraints greater. Thus, previous estimates of the cost of regulation may no longer be applicable in todays economy. I exploit changes in regulations following the CAA Amendments of 1990, in which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adopted new and more stringent pollution standards. My estimates from these most recent revisions are arguably more applicable to current policy debates, and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light of the EPAs recent proposal to further strengthen emissions standar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2010).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环境规制和劳动力重新分配:清洁空气法案的证据
里德·沃克
摘要:本文采用由人口普查纵向业务数据库(LBD)提供的最新工厂监管状况的数据来衡量环境规制对行业就业水平的影响。各种规范表明,环境规制紧张局势的变化与就业增长以及各个行业的水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首选估计表明,由于1990年“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的出台,县级监管状况的变化使受监管部门的规模在10年内减少了15%。
环境规制限制污染空气的废气的排放是对健康益处的。 与这些优势相关的是降低污染的成本。“减排成本和支出调查”显示,与美国“清洁空气法案”相关的法规在资本支出中的投资额近50亿美元,制造业的年度运营成本约为200亿美元 (美国人口普查局2008)。 因此,制造商经常认为,这些规定使工厂和工业处于竞争劣势,迫使工厂规模缩小或倒闭。 在这个论点中隐含的是,环境规制导致与行业广泛的产出下降相关的失业。
因此,各种论文都研究了环境规制对被监管行业的影响,通常发现环境规制对行业就业的具有负面影响(Vernon Henderson 1996,Michael Greenstone,2002)。然而,环境规制通常会影响劳动力在行业之间的分配,而不是经济范围内的就业水平(肯尼思·阿尔,迈伦·克劳珀,乔治·艾德,罗伯特·哈恩,莱斯特·拉夫,理查德·诺尔,保罗·波特尼,米尔顿·罗素,理查德·施马辛塞,凯利·史密斯和罗伯特Stavins 1996)。因此,对员工的监管成本的恰当的衡量标准不应以失业的工作为特征,而应归功于重新分配生产或工人的任何过渡费用(Arrow et al。1996,Greenstone 2002)。只要员工从一个雇主转为下一个工作岗位,而不会因工作具体的人力资本或失业而蒙受损失,那么在评估环境规制时就不应该是失业人员的净成本。尽管许多论文中已经指出了这一事实,但是很少甚至没有论文试图在环境规制方面理解这些摩擦的程度。
本文的目的是开始了解“清洁空气法”(CAA)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管强度变化对受影响劳动力的高效工作过程的贡献程度。最近将工厂级工作统计数据与工作人员职位周转调查相联系的研究已经发现工厂级工作减少与非自愿职工失业之间存在很大的联系(Steven Davis,Jason Faberman&John Haltiwanger,2006年),裁员可能导致重要的非就业损失和盈余损失(参见Till Von Wachter,Jae Song&Joyce Manchester(2009)最近的证明)。因此,公司利润率调整幅度对劳动力具有重要的分配影响。如果企业通过增加环境税率(裁员)来调整劳动力需求,降低招聘率(工作减少),减少工厂进入率或增加工厂退出率,工人将会或多或少的受到裁员和就业机会减少等人力资本相关的影响。
这是将环境规制中的就业净变化分解为工作流动的第一篇文章,为环境规制对劳动力的分配影响提供了新的见解。在过程中,我借鉴了有关工厂一级监管状况的最详细和全面的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机密级别的纵向数据库,我可以链接到环境保护局的工厂级监管数据库。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可以明确地观察行业环境规制的情况,并观察这些行业对环境规制变化的反应。以前推测环境规制强度的工作是基于全国二和四位数的行业分类。
进一步的贡献是目前还没有对CAA关于就业的最新修订和更改的研究。以前研究估计CAA成本的工作侧重于较早期污染更严重,技术水平更低的时候。因此,以前的环境规制成本的估计可能不再适用于今天的经济。我在1990年的“民航处修正案”中利用了条例的变更,环境保护署(EPA)在其中采取了新的更严格的污染标准。根据这些最新修订的估计,更适用于当前的政策条件,并且鉴于了EPA最近关于进一步加强排放标准的建议(环境保护局2010年),这一点尤其重要。
结果表明,1990年代初期加强排放标准导致受影响部门就业率持续下降。行业水平模型显示,环境规制变化后的十年内,新兴规范污染行业的规缩小了15%以上。这些就业变化主要是由于工厂级别的裁员增加,这表明这些工厂级别的下降与非自愿失业有关的工人级别调整成本有关。
1美国的环境规制现状
美国的空气污染管理工作由县级以下监管严格性的CAA协调。规制主要影响人们生活和工作的人口稠密地区以及减排潜力较大的地区。虽然各县的监管情况各不相同,但也有7个“空气污染物标准”不同,具有特定空气污染物含量高的地区仅针对该污染物进行管理,污染物过量污染的阈值因各污染物而异,但在任何一年中,一些县发现自己超过了这些门槛,而另外一些县却没有。
环境空气污染是由EPA污染监测仪测量的,可以对每种污染物进行小时/每日的污染监测。监测位置不受地方当局的操纵。当一个县污染物排放超标时,环保局强制要求排放该污染物的当地工厂采用“最低可实现的排放率”(LAER)技术,而不考虑成本。此外,EPA强制任何新的污染工厂希望在该特定的县定位,从县内另一个污染源排放,相比之下,在指定为“达到”的地区,大型污染厂必须使用“最佳控制技术”(BACT),这显着减少总而言之,在不合格领域,企业受制于旨在减少排放而不考虑成本的法规,达到程度得到较轻微的监管。
1990年,国会通过了“清洁空气法”的一系列修正案。 1990年修正案为PM-10.1制定了新的标准污染物污染物类别。此外,EPA正式审查了所有标准污染物的所有县级不合格标识。因此,1991年有177个县和3915个工厂转为不合格。
2纵向工厂级就业和环境规制数据
该项目的主要数据来源是人口普查局的纵向业务数据库(LBD),这是一个涵盖美国企业范围的企业级纵向数据库。包括各个机构的就业,工资,年龄,详细的行业,位置,入/出年度等。我将LBD与工厂级别监管和允许使用名称和地址匹配算法称为空中设施子系统(AFS)的EPA的数据进行了联系。[2]
AFS提供许可证信息,详细说明了工厂受到监管的监管计划以及颁发许可证的具体污染物。 AFS的限制即它不提供有关这些许可证什么时候发出的信息。幸运的是,CAA的监管结构可以根据县的不合格状况推断出时间。特别地,我把在AFS数据库中具有经营许可证,但许可证上不符合特定污染物的工厂定义为是受到环境规制的。这是第一个包工厂级环境规制现状的纵向国家数据集。以前的研究通过二位数和四位数的SIC等级的国家污染估计来进行调控(Greenstone 2002,Becker,2005)。
我选择制造和公用事业部门内的机构作为样本。我还排除了样本框架内任职人数不足50人的企业和寿命不到3年的机构。由于EPA法规主要适用于每年可能排放超过100吨的主要来源,不包括这些对估计结果影响不大的小型机构。
我创建了第二个数据集,按年份将1985-2005年的工厂级的微观数据(即污染或无污染)进行分类。这减轻了计算负担,并提供了对连续工厂的就业变化以及与工厂进入或退出有关的任何变更的总体统计数据。
2.1总结统计
数据中存在着巨大的监管变化是由于美国农业部根据县一级管理并且只有污染工厂受到监管。 因此了解这些变化来源的正交程度到工厂或县层面是有意义的。 如果实施环境规制前后县或工厂之间有显着差异,那么这些差异就是适当经验规范的选择。
表1:CAA修正案之前县和工厂的就业特征(1990年)
注意:工厂水平增长率和劳动力重新分配率是使用(Steven Davis&John Haltiwanger 1992)的方法,并在第4节进一步描述。每个类别的县数:2265,Nonattain 392,Switch 177。
表1列出了样本县和工厂样本中污染和无污染部门,每栏列出了1991年实现县,未实现县和切换不了状况的县的特点。不成比例县往往在经济上更加城市化,依靠横断面变化可能会混淆规定与各县的其他异质来源。同样,受监管工厂纯粹依靠时间序列的变化认为1990年代初的衰退与1990年CAA修正案同时发生。同一县内工厂之间的比较发现除了环境规制状态,污染和无污染工厂是相似的。表1显示,污染工厂往往比他们的同行规模更大,资历更老,但增长速度较慢。不能解决这些差异可能导致与工厂资历或工厂复古效应调节混乱,这一点在以前的文献中没有提到。
可信的识别需要考虑所有这些观察和不可观察的来源混杂因素。 幸运的是,丰富的数据允许我灵活地控制大多数数据不可观察的冲击 ,同时仍然能够恢复精确的估计。
3部门级动态
为了了解CAA法规对行业层面就业的动态影响,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分布式滞后模型
其中yjct表示第t年c县的行业j就业的对数。 Nck表示实施监管前后的k年度县级以上行业指标,Pj为部门污染水平指标。还包括县域固定效应(delta;jc)所有估计数都是基于不符合条件之前和之后的部门比较指定并且用逐年线性趋势(zeta;ct)来解释可能会混淆的不可观察的县趋势。最后,回归由1985年每个县/部门总就业加权。
感兴趣的参数是beta;k这提供了关于环境规制变化的就业半弹性的估计。 beta;k的估计是在经历变化的部门之后,通过部门间比较来确定监管力度。本规范控制任何可观察或不可观察的永久物县域特色以及影响污染的所有县级趋势非污染部门。考虑到跨部门之间的潜在相关性县县标准误差集中在县级。
图1绘制了5年前的等式1版本的系数和1990年CAA修正案后的10年。具体来说,绘制系数是县级污染部门在事件时间指标的差异,这改变了1991年相对于没有改变的县的不达标状态,控制县级线性时间趋势和县级固定效应。
图1:监管前后的行业层面就业估算
注意:绘制的是等式1版本的系数估计值。详细信息请参见文本。虚线代表95%置信区间。
这个图中有两个重要的特点。 一,就业趋势变更前几年的污染部门是相似的。其次,从监管变化的这一年开始,在实施新环境规制的县,污染部门就业率在之后的8年间比1990年下降了15%。 回想一下,这些估计是相对的在1990年没有改变监管状态的县的污染部门,因此任何周期性的与1990年代初期经济衰退有关的差异应予以考虑。 图1总结了论文的主要发现:即不合格指定之间存在着强烈而持久的关系和部门级就业。我接下来就工厂层面间隔时间为5年的数据观察就业增长和劳动力重新分配的差异。当允许我使用“制造商普查”(Henderson 1996,Greenstone 2002)将我的估计与以前的文献进行比较时,发现关注焦点将中长期差异从短期动态中抽象出来。
4工厂级劳动力再分配率
根据文献,我将工厂就业增长定义为t和t-5之间的就业差异除以这两个时期的平均就业水平。 为了更好地了解企业调整的利润,就业增长分为两个部分:一个衡量增长机构增长率(即创造就业率),另一个衡量订约机构缩减的速度(即裁员率).我选择以下工厂级别的形式:
其中Nct-5是五年前c县是否不达标的滞后指标,Pi是污染状况的工厂水平指标。 参数theta;提供了工厂级别不合格指定对5年工厂就业增长和劳动力重新分配率影响的估计。 公式2还控制了具有2位SICtimes;年固定效应(delta;jt)的行业年度波动; 任何具有工厂固定效应(eta;i)的永久观察或不可观察工厂特征; 以及影响污染和无污染工厂的地方经济冲击,同样包括按年度固定效应(zeta;ct)。 由于工厂资历是增长率和工作流动的重要决定因素,我还包括一套工厂资历指标(gamma;it)。 最后,估计值以样本工厂特定中位数为中心。
表2的A组显示了与方程2有关的回归估计。与以前文献中的结果相似,工厂级就业增长随着工厂监管水平的增加而下降。 有趣的是,结果表明,大部分调整是通过增加就业率(即工业就业负增长,工厂就业率下降)来实现的。 新受监管的工厂的裁员率几乎翻了一番,这表明劳动力从工厂级的就业减少中存在着显著的成本。
表2:不符合指定的工厂5年劳动力重新分配率的影响
注意:此表格报告了与方程式2有关的几项估计,其中每个面板的每列都是单独的回归。 详情请见文字。 N = 470958。括号中列出了在县级群集的强大的标准错误。
由于各县可以对各种污染源进行管理,而且环境规制只应用于发布有关污染物的工厂,我可以假设一个包含了每种污染物的监管效果的模型(Greenstone 2002)。 我估计一个版本方程2,其中有四个感兴趣的参数,对于pisin;{CO,PM10,O3,SO2}的theta;p,取决于相应的不确定指标,Npct-5等于1。因此,调节效应应该被定义为对每种污染物p的工厂水平调节状态的变化,以该工厂排放污染物p为条件。 表2的B组显示了联合污染物估算的结果。 行业环境规制状况的变化对所有污染物类别的就业增长和劳动力重新分配率都有重大影响。
5结论
这里的证据表明,企业主要通过裁员而不是降低招聘率来应对环境规制的压力。重要的是,Davis,Faberman&Haltiwanger(2006)最近的工作显示,工厂层面的裁员程度很高,这些行业的非自愿裁员的百分比很高。他们的工作结合本文的结果表明,政策冲击后重新分配劳动力的调整成本可能很大。
未来的工作应该尝试明确估算这些成本。具体来说,纵向微数据可以显示出在短期和长期内受影响劳动力重新分配的收入损失幅度。大多数规定发生在劳动力较多的市场(即更多的城市地区),由于这些冲击是非常具体的部门,因此劳动力的实际成本可能相当适中。参见Walker(2010)在美国使用的匹配的雇主雇员数据。
参考文献
[1]Arrow, Kenneth, Maureen Cropper, George Eads, Robert Hahn, Lester Lave, Richard Noll, Paul Portney, Milton Russell, Richard Schmalensee, Kerry Smith, and Robert Stavins. 1996. “Benefit-Cost Analysis in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afety Regulation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7744],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