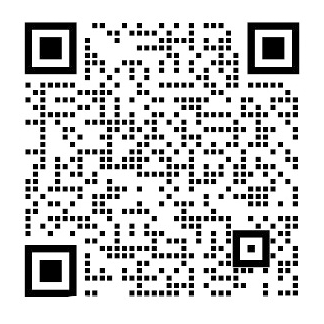有无政治集权的联邦制:中国对比俄罗斯
OLIVIER BLANCHARD AND ANDREI SHLEIFER
摘要:在中国,地方政府为新企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俄罗斯,无论是通过税收、监管还是腐败,地方政府通常都会从中作梗。我们认为,这种差异可以追溯到中国目前的政治集权程度,而不是俄罗斯。在中国,中央政府足够强大和有纪律,足以促使地方政府支持经济增长。在俄罗斯,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同意,但有一个重要的警告。我们认为,俄罗斯的经验表明,另一个因素至关重要,即政治中央集权。[JEL P30,P50]
关键词:关键词1; 关键词2; 关键词3;关键词4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世界上最高的速度增长,俄罗斯是最低的国家之一。差异主要来自新私营部门的增长。在中国,新的私营部门蓬勃发展。在俄罗斯,它停滞不前。为什么私营部门的发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在这两个国家,证据表明了地方政府行为的重要性。在中国,地方政府为新企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Oi, 1992; Qian and Weingast, 1997)。在俄罗斯,无论是通过税收、监管还是腐败,地方政府通常都会从中作梗(Shleifer,1997;约翰逊,考夫曼和施莱弗,1997年;麦肯锡,1999;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1999年)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世界上最高的速度增长,俄罗斯是最低的国家之一。差异主要来自新私营部门的增长。在中国,新的私营部门蓬勃发展。在俄罗斯,它停滞不前。为什么私营部门的发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在这两个国家,证据表明了地方政府行为的重要性。在中国,地方政府为新企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Oi,1992;钱和温加斯特,1997)。在俄罗斯,无论是通过税收、监管还是腐败,地方政府通常都会从中作梗(Shleifer, 1997;Johnson, Kaufmann, and Shleifer, 1997; McKinsey, 1999; and EBRD, 1999)[1]
关于俄罗斯地方政府的态度,主要有两种假设。第一个——称之为“俘获”——是地方政府被最初的租金持有者俘获,主要是被转型前主导俄罗斯经济的旧公司俘获。根据这种观点,地方政府既努力向这些公司转移资金,又保护它们免受新公司的竞争。第一种观点认为,他们对新私营部门的敌对态度是蓄意的。第二种观点——称之为“租金竞争”——认为地方政府的行为反而是行政混乱的意外结果。太多的机构试图从新的私人公司那里榨取租金,使得创建或经营私人企业无利可图,至少在法律上是这样。[2]
两条解释似乎是合理的,并不相互排斥,但它们提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即为什么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这里又有两个主要假设。
第一种观点,中国的初始租金持有者比俄罗斯弱。中国从非常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开始转型。其农业不依赖大型集体农场,其工业的大型企业相对较少。相比之下,俄罗斯开始转型时是一个完全工业化的经济体,由大型国有企业和集体农场主导。根据这种观点,中国被抓获的可能性比俄罗斯更有限。
第二种观点指向中国中央政府的实力。中国的过渡是在共产党的严密控制下进行的。因此,中央政府在奖励或惩罚地方政府方面处于强势地位,降低了地方兼并的风险和租金竞争的范围(Huang,1998)。相比之下,俄罗斯的转型伴随着新兴民主的出现。中央政府既没有强大到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也没有强大到对增长收益的分享制定明确的规则(Shleifer和Treisman,1999;Treisman,1999年b)。因此,地方政府没有什么动机来抵制占领或控制租金竞争。
本文的目的是探讨最后一个论点,更一般地说,是探讨联邦制在转型中的作用。这个问题很重要。根据中国的经验,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联邦制可以在发展中发挥核心作用(特别见Qian and Weingast, 1997; Roland, 2000)。事实上,一个新的术语“市场保护联邦制”已经被创造出来,以强调分权对中国增长的好处。我们同意,但有一个重要的警告。我们认为,俄罗斯的经验表明,另一个因素至关重要,即政治中央集权。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呼应了Riker (1964)首先提出的一个主题:要让联邦制发挥作用并持续下去,它必须伴随着政治中央集权。
一、联邦制和激励模式
我们首先写下一个联邦制和地方政府激励的模型。该模型非常简单,但它提供了一种查看事实和讨论问题的便捷方式。这是我们在接下来的两个部分中要做的。
把政府想象成有两个层次:中央和地方(换句话说,暂时忽略俄罗斯和中国至少有三个相关的政府层次:中央、地区和地方)。
假设每个地方政府都面临一个简单的选择。它可以通过限制向国有企业和前国有企业转移资源,允许新的私营企业进入和发展,从而促进增长。或者,它可以通过将资源转移到旧公司和/或阻止新公司的创建来扼杀增长。
为什么地方政府会选择第二种选择?根据“捕获”观点,它可能想保护国有或前国有企业免受竞争。根据“租金竞争”的观点,它可能根本无法阻止地方官员的贿赂和腐败。理清两者的相对重要性应该是研究议程上的重点,但在这里并不重要。就我们的目的而言,两者都有相同的含义:没有增长。
设y为增长下的额外产出。通过适当的正常化,让y也代表增长中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可获得的额外收入。让b成为当地政府扼杀增长的私人利益。根据俘获解释,b可能反映从现有公司向地方政府的转移,以贿赂、现金或实物支付的形式。在租金解释的竞争下,b可能反映地方政府减少或协调地方官员受贿的成本。
现在转向中央政府。假设(我们稍后将回到这一假设)中央政府希望促进增长,并认为中央政府有两个主要工具,胡萝卜和大棒:
收入共享(胡萝卜):中央政府可以选择与地方政府共享收入的程度。假设a是地方政府从额外增长中获得的收入份额:如果一个地方政府选择促进增长,它就获得了收入。·
政治集权(大棒):中央政府可以影响地方政府继续执政的概率,以享受增长带来的收入或扼杀增长带来的私人利益。用px表示地方政府在扼杀增长的情况下仍然掌权的概率,用py表示促进增长的相应概率。定义p = py/px。p值显然首先取决于地方官员是任命还是选举产生的。如果他们被任命,那么大概中央政府可以自由选择p,并让它达到它想要的高度。如果他们当选,结果取决于中央政府通过认可和支持特定候选人来影响选举结果的能力。如果中央对结果几乎没有控制权,而且俘获很重要,那么p可能小于1:如果地方政府扼杀增长,而不是促进增长,那么它可能更有可能保持有和无政治集权的联邦制。所有需要做的就是让现有公司在政治上比新企业家组织得更好。
在这些假设下,如果py a y gt; px b,或者等价地,如果
p a y gt; b. (1)
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选择增长,大棒越强(p越高),胡萝卜越大(a越高),增长潜力越大(y越高),捕获的收益越小或控制租金竞争的成本越低(b越低)。这个公式为组织俄罗斯对中国的讨论提供了一种方便的方式。
二、增长、税收共享、政治集权和其他问题
在继续研究模型各种参数的经验证据之前,人们很可能会质疑这样一种假设,即中央政府是支持增长的,或者至少比地方政府更支持增长。当然,中国和俄罗斯都提供了许多中央政府政策摧毁经济的例子。然而,在转型和变革的背景下,认为中央政府不太可能被初始租金持有者俘获的假设似乎是合理的。相对于国有和前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规模较小,更直接地受到关闭特定企业的失业影响,更有可能对转移或保护请求做出积极回应。中央政府也可能被俘获,但不一定被反对增长的团体俘获。例如,被“寡头”占领很可能会导致财富的大规模再分配,但不一定会降低增长。[3]
以前的许多研究都集中在y上。如果增长前景非常好,那么让新企业进入并促进增长是有吸引力的。这里想到了莫斯科及其市长卢日科夫的例子。但如果增长前景暗淡,相对于保护老企业,允许新企业进入和增长的回报可能会很低,y可能会很小。[4]如果促进增长政策的改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而现任政治家不太可能从中受益,这种可能性尤其大。
如果y很小,该中心可能无法说服地方政府选择增长。即使a和p的值很大,也不能改变不等式。
最近的一些研究为俄罗斯和中国提供了关于a的一些证据。在对中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财政关系的计量经济研究中,Jin, Qian, and Weingast(1999)发现边际a值很高,约为0.8。(在描述证据时,我们需要区分三级政府:中央、地区和地方。)对于中国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没有相应的研究。Wong (1997)认为,地方政府和地区政府之间合同的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可能类似于中央政府和地区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对俄罗斯地方政府和地区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计量经济学研究中,Zhuravskaya(2000)发现,边际a仅为0.1左右,这给地方政府增加税基的激励很弱。俄罗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没有相应的研究。然而,在个人通信中,特雷斯曼报告称,从与金Jin, Qian, and Weingast(1999)的规格相似的回归中获得的俄罗斯的a估计值并不低于中国。
总而言之,证据有些模糊。在地方层面上,中国的a值可能略高于俄罗斯。然而,根据现有证据,似乎很难得出结论,即a的差异足以解释俄罗斯和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差异。
最后再看p,如果追求增长政策,保持执政的相对概率。在中国,共产党有权任命和罢免省长,它行使这一权力既支持那些经济表现良好的地区的省长,也惩罚那些遵循反增长政策的省长(见黄,1998)。也许作为最终的奖品,那些地区表现良好的州长已经被纳入北京的国家政府。很明显,在中国,p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如果共产党的权力被视为绝对的,那么p接近无穷大。
在俄罗斯,州长现在是选举产生的,而不是任命的。国家政府通过行政和选举支持奖惩州长的能力有限。因此,俄罗斯的p远低于中国;可以说,这个数字还不到1。
因此,这种政治控制上的差异,而不是收入分享安排上的差异,可能是不平等(1)适用于中国而不是俄罗斯的原因。对于足够高的p,即使是低a也可能维持增长政策。中国中央政府允许大部分税收收入和支出责任留在这些地区,但鉴于其任命权,它可能会以较低的a值逃脱惩罚。另一方面,对俄罗斯政府来说,一个能引导地方政府促进增长的计划可能没有任何价值。因此,不管怎样,中央政府可能没有什么动力来维持高价值的货币。
根据这一模式来考察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的演变是很有趣的。在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中央政府依赖于在大多数地区使用agt;1。 为此,它对几个产油区征税,并利用赤字财政来弥补中央联邦制在有无政治集权的情况下产生的净收入不足175(Treisman,1999a)。在这段时间里,特别是在1992-93年间,叶利钦对州长也有行政控制权,所以p比之后更高。Treisman(1999a)所示,这项政策在一段时间内运作良好,并为该地区带来了中心和平。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种平衡崩溃了。首先,稳定政策迫使中央政府减少了大部分地区的财政赤字,因为中央赤字必须减少,因此无法负担向各州的大笔转移。第二,政治分权和无党派州长选举显著降低了p。第三,持续的衰退至少降低了y的预期。在今天的俄罗斯联邦结构中,方程式(1)失败了,部分原因是a可能很低,但更重要的是,p很低。回到Riker(1964年),今天俄罗斯所特有的边缘化联邦制可能根本不可持续。
我们对俄罗斯政党实现或不实现政治集中的作用的关注可能过于狭隘。在俄罗斯,两种力量至少已经部分替代。首先是国家媒体。俄罗斯的媒体公司是私营的,由与政治运动密切相关的利益集团控制,特别是政府和中左翼反对派。媒体集团积极利用电视和报纸,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当时两人都支持Yeltsin)中,尤其是在1999年的杜马选举中,让他们喜欢的候选人当选。第二个集中力量是能源垄断企业,尤其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联合能源系统公司。第一家垄断了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第二个控制着电网。这两家公司虽然名义上是私营的,但与政府关系密切。这两种能源都被政府用来向合作地区提供廉价能源和免费能源。通过这种方式,两者都被用来使地区政府的行为更能响应该中心的需求。然而,这些替代品的效率或可取性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三、 讨论和影响
我们的分析对中国、俄罗斯以及联邦制的经济理论都有很多启示。关于中国,我们的分析表明,在联邦制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有益作用的程度上,这种联邦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共产党的中央集权作用。[5]如果共产党在未来掌权时,没有被影响州长任命或选举前景的其他国家政党取代或补充,p将下降,导致其联邦安排中更大的寻租和更低的效率。我们的分析给中国的信息很明确:中国学者强调的“维护市场的联邦制”的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集中。lt;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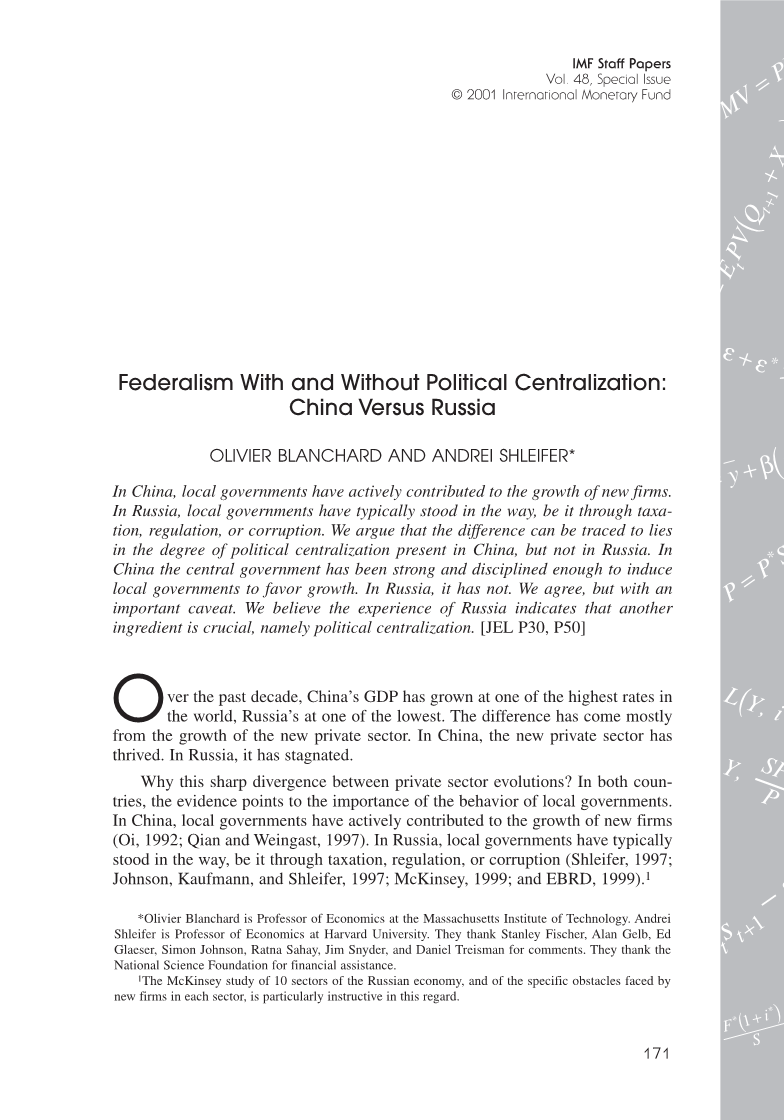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9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597975],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