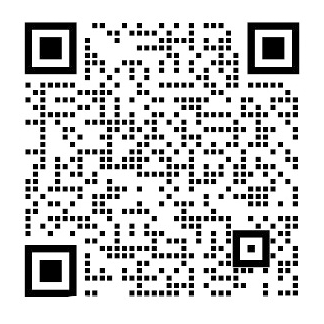TWO PATTERNS: TEACHING FOR SKILL EFFICIENCY AND TEACHING FOR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Two of the most valued learning goals in school mathematics are, and have been for some time, skill efficiency and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Resnick amp; Ford, 1981). By skill efficiency, we mean the accurate, smooth, and rapid execution of mathematical procedures (see, for example, skill learning in Gagne, 1985). We do not include the flexible use of skills or their adaptation to fit new situations. By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we mean mental connections among mathematical facts, procedures, and ideas (Brownell, 1935; Davis, 1984; Hiebert amp; Carpenter, 1992). This definition suggests that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grows as mental connections become richer and more widespread. As we mentioned earlier, considerable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to identify the kinds of teaching that facilitate studentsrsquo; achievement of these two learning goals.
An initial and rather obvious finding is that some kinds of teaching support skill efficiency and other kinds of teaching support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That different kinds of teaching facilitate different kinds of learning is a direct consequence of opportunity to learn. Different kinds of teaching provide different opportunities to learn that, in turn, yield different kinds of learning. This notion has been expressed for some time. Here is what Edward Thorndike had to say in 1912, “It is possible, by focusing attention upon immediate facility, to choose methods of teaching that are excellent for that, but defective for the more important service of arousing in a pupil the desire and power to educate himself ”. Gagne (1985) refined the notion by detailing different instructional techniques appropriate for different learning out- comes. And Brophy (1988) reminded educators that the work he reviewed linking teaching behaviors to studentsrsquo; learning mostly had used measures of routine skill learning. Other teaching features might have been identified if other learning outcomes had been used.
The story gets more complicated when one notices that neither theory nor empirical data indicate a simpl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one method of teaching and skill efficiency and between another method of teaching and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The best way to express current knowledge in the field is to describe some features of teaching that facilitate skill efficiency and some features of teaching that facilitate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and to indicate where these features overlap or intersect.
At this point we should recognize an important historic distinction that is related to but different from the distinction in learning goals we are making here. In a classic book on learning and teaching, Ausubel (1963) proposed a 2times;2 matrix with rote versus meaningful learning on one axis and discovery versus expository teaching on the other axis. Ausubel contended that these dimensions were independent. Expository teaching, said Ausubel, does not necessarily produce rote learning, and discovery teaching does not necessarily produce meaningful learning. We agree with Ausubel and raise the distinction here for two reasons. First, we want to alert readers that we are not necessarily linking skill efficiency with expository teaching. Based on our definition, skills might be executed efficiently under rote or meaningful learning conditions.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on the other hand, would require meaningful learning.
A second reason for raising Ausubelrsquo;s (1963) distinction is that we do not expect the features of teaching that facilitate skill efficiency and conceptual under- standing to fall neatly into categories such as “expository” or “discovery.” In fact, the features of teaching we describe do not fit easily into any of the categories frequently used to describe teaching: direct instruction versus inquiry-based teaching, student-centered versus teacher-centered teaching, traditional versus reform-based teaching, and so on. Although these categories and labels have been useful for some purposes because they capture constellations of features and treat teaching as systems of interacting components, they also can be misleading because they group together features in ill-defined ways and connote different kinds of teaching to different people. For our purposes, avoiding past connotations is important. In fact, we will argue that most of these categories, distinctions, and labels are now more confusing than helpful, and further advances in research as well as clarity of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ill benefit from abandoning these labels.
But abandoning the usual labels for methods or systems of instruction in favor of identifying features of teaching that link with learning appears to violate a principle we espoused earlier—teaching is a system of interacting elements, and the effects of an individual feature are determined by the system of which it is a part. Can these two points of view be reconciled? Can researchers single out features of teaching that facilitate learning and still believe that the specific effects of individual features depend on the systems of teaching in which they operate? We think so, for two reasons. First, by looking for patterns across multiple studies, we are searching for features that replicate their effects through different implementations of similar systems and even through different systems. We suspect that the exact effects of target features vary somewhat from system to system, but we expect some of these features to emerge as sufficiently robust across systems to appear as detectable patterns. Second, we assume that when we identify specific features of teaching we actually are identifying clusters of features. The features we single out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probably operate within a supportive set of less apparent features. The regularity that can be detected in their effects on studentsrsquo; learning might be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两种模式:技能效率教学模式和概念理解教学模式
在学校数学中,两个最有价值的学习目标是技能效率和概念理解,并且长久以来一直如此(雷斯尼克和福特,1981)。所谓技能效率,是指准确、流畅、快速地执行数学程序(例如,参见加涅,1985年的技能学习)。这不包括技能的灵活运用或适应新的情况。通过概念上的理解,可以发现我们指的是数学事实、程序和思想之间的心理联系(布朗内尔,1935年;戴维斯,1984年;希伯特和卡彭特,1992年)。这个定义表明,随着心理联系变得更丰富和更广泛,概念的理解也进而增长。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来确定促进学生实现这两个学习目标的教学类型。
一个初显成效的发现是,某些类型的教学支持技能效率,而其他类型的教学则支持概念理解。不同种类的教学促进了不同种类的学习,这是学习机会的直接结果。不同种类的教学提供不同的学习机会,进而产生不同种类的学习。这个概念已经表达了一段时间。这就是爱德华·桑迪克在1912年所说的话:“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即时设施上,可以选择优秀的教学方法,但激发学生教育自己的欲望和力量是有缺陷的。”加涅(1985)通过详细描述适合于不同学习结果的不同教学技术来改进了这个概念。布罗菲(1988)提醒教育工作者,他所复习的将教学行为与学生的学习联系起来的工作主要采用了常规技能学习的方法。如果使用了其他学习成果,则可能已经确定了其他教学功能。
当人们注意到理论和经验数据都没有表明一种教学方法和技能效率之间以及另一种教学方法和概念理解之间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时,故事就变得更加复杂。表达本领域当前知识的最好方法是描述一些有助于提高技能效率的教学特征和一些有助于概念理解的教学特征,并指出这些特征在哪些地方重叠或相交。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重要的历史区别,该区别与我们在此处制定的学习目标的区别有关,但与之不同。在一本关于学与教的经典著作中,奥苏贝尔(1963)提出了一个2times;2矩阵,其中一个轴是死记硬背对有意义的学习,而另一轴则是发现与说明性教学。奥苏贝尔认为这些维度是独立的。奥苏贝尔说,说明性教学不一定能产生死记硬背的学习,发现教学不一定能产生有意义的学习。我们同意奥苏贝尔并在此提出区别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我们要提醒读者我们不一定要将技能效率与说明性教学联系在一起。 根据我们的定义,技能可能在死记硬背或有意义的学习条件下有效地执行。另一方面,对概念的理解需要有意义的学习。
使得奥苏贝尔(1963)与众不同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并不期望能够提高技能效率和概念理解的教学功能会巧妙地归入“说明”或“发现”之类的类别。实际上,我们所描述的教学特征并不容易融入经常用于描述教学的任何类别:直接教学与探究式教学,以学生为中心与以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传统与基于改革的教学等等。尽管这些类别和标签由于可以捕获要素群并将教学视为相互作用的组件系统而在某些方面很有用,但它们也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它们以不明确的方式将要素归类在一起,并向不同的人暗示着不同种类的教学。就我们的目的而言,避免过去的含义很重要。实际上,我们将争辩说,现在这些类别,区别和标签中的大多数现在变得更加混乱而不是有用,并且研究的进一步进展以及政策建议的明确性将受益于放弃这些标签。
但是放弃教学方法或教学系统的常规标签,而去识别与学习联系在一起的教学特征,似乎违反了我们先前所倡导的原则-教学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系统,而单个特征的作用则取决于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两种观点可以调和吗?研究人员是否可以挑选出有助于学习的教学功能,并且仍然相信各个功能的具体效果取决于他们所从事的教学系统?我们这样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通过在多个研究中寻找模式,我们正在寻找通过相似系统的不同实现甚至通过不同系统来复制其效果的特征。我们怀疑目标特征的确切效果因系统而异,但是我们希望其中一些特征在整个系统中表现出足够的鲁棒性,从而表现为可检测的模式。其次,我们假设当我们确定教学的特定特征时,实际上是在识别特征簇。我们在以下各节中挑选出的功能可能会在一组不太明显的功能中相互支持。在对学生学习的影响中可以发现的规律性可能是一系列功能在一系列教学系统中运作良好的结果。由于经验数据尚无法进行更精确的解释,因此我们选择了教学的特定功能。但是,教学系统的假设预测这些特征仅仅是周围集群最显着的方面。也许更先进的研究工具的发展将在将来提供更精确的描述。
高效地执行技能
我们没有任何研究经验来检验哪些教学特征支持技能效率以及哪些要素支持概念理解。 研究对比了强调技能与理解的教学方法,但是没有一个研究或一组研究旨在优化这些方法 两个学习成果,并理清与每个学习成果相关的教学特征。此外,不同的研究人员使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因此必须通过解释设计和结果并诱导一致性来抽象研究模式,而不是简单地将发现相加。
20世纪70年代,远西部地区教育研究与发展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重点是将教师的行为与学生在数学和阅读方面的成绩联系起来。这项研究被称为开始教师评估研究(BTES),尽管在实践中,这些研究涉及到至少有3年经验的教师,并集中于研究而不是评估。有趣的是,没有一个被衡量的教师行为都是学生在数学和阅读中学习的重要预测因素。这一发现使一些重要的教学行动是内容特定的。
BTES关于数学教学的结果往往与之前引用的研究一致,但在个别学生层面检查数据时增加了一些有趣的发现。研究发现,学生在标准化成绩考试中的成绩与在课堂课程中从事数学工作(除了偶尔的错误外的正确答案)之间存在积极的关系。相反,当学生从事低成功率的活动时,就存在着一种消极的关系。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一个足够重要的发现,可以完善机会的概念,即“学生从事与他的预期学习相关的学术任务的时间”。有趣的是,这些研究中对高成功率的关注为良好和群体提供了理由,强调了学生在独立工作前为座椅工作做好充分准备的重要性。BTES中的研究概述可以在鲍威尔(1980)中找到,以及麦当劳和埃里亚斯(1976)的五卷最终报告中提供的详细描述。
从刚刚回顾的研究中得出的教学特征可以概括如下:促进技能效率的教学迅速加快,包括教师建模和许多教师指导的产品类型问题,并且显示出从演示到实质性的平稳过渡 大量的无差错练习。 在这一系列功能中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在组织,调整节奏和呈现信息以达到明确定义的学习目标方面所起的核心作用。
上面确定的教学功能可以提高学生的技能效率。 这些功能对学生的概念发展有何影响尚不清楚。由于概念理解在数学教育中引起了极大兴趣,并融合了最近构想的数学熟练度目标(国家研究委员会,2001年),因此我们在下一部分中将大量空间用于检查教学与学生对概念理解之间的联系。
发展概念上的理解
我们将概念理解定义为数学事实,过程和思想之间的精神联系。这个简单的定义可以很好地满足我们的目的,但并非没有争议。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个定义过于强调个人的内部或心理表征,应该考虑社会文化因素。从这种社会文化的观点来看,理解可以看作是参加在该行业的实践中变得有能力的人们社区的一种活动。在我们的情况下,这意味着要参加一个由一群人组成的社区,他们不仅善于做数学并具有一定的数学意义,同时也重视这种活动。我们认为,理解的精神联系和文化参与观点都可能是有用的,并且我们在以下各节中提出的主张在任何一种定义下都是合理的。但是,由于我们回顾的研究示例是在当时普遍存在的心理联系视图中进行的,因此在阅读下一部分时应牢记此定义。
促进概念发展的教学:两个关键特征
教育工作者一直对促进概念理解一直很感兴趣,至少在他们的修辞学上如此,但是最近对该主题的兴趣激增了。 在我们起草本段的当天,亚马逊网站找到了90,448本书条目,它们的术语是:理解教学。 最畅销的书名包括“音乐理解教学”,“工作策略:提高理解能力的教学”和“没有恐惧的莎士比亚:理解教学”。 包含与本章内容相关的两本著名书籍是科恩,麦克劳克林和塔尔伯特(1993)编辑的《理解教学》和芬内马和伯格(1999)编辑的《促进理解的数学教室》。显然,该主题并不缺乏分析和建议。
特征1:师生明确参与概念
在许多方面,人们声称如果教师明确地学习数学概念,学生将获得对数学的概念性理解,这是对一般观点的重述,即一般认为,学生将学习他们拥有最佳学习机会的东西。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很明显,甚至可能不是很有趣。但是,当人们发现该主张得到广泛研究设计的支持并在不同的教学方法或系统中成立时,就变得更加有趣。我们审查相关的研究,以及从中获得这些研究的较大文献,都显示出显着变化。
我们认为,证据不足以证明单一或“最佳”的教学方法可以促进概念性理解。但是我们认为数据确实支持教学功能,这可能是许多方法的一部分:要明确关注数学的概念发展。
为了支持和阐明该主张,我们选择了以下这组研究进行复习,因为它们关注相同的数学主题-小学年级中的多位数字加减法-但使用不同的研究设计实施了完全不同的处理方法。菲森(1990)研究了一种特殊的概念性教学方法使得学生获得标准加法和减法算法。他对169名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进行了专门设计的加法指导,其中75名二年级学生也得到了减法的特别指导。指令包括使用10进制块的算法的仔细演示,并特别注意当数字增加到三位数和四位数时的重组模式。物理表示法和书面表示法之间明确地建立了联系。一些教师使用全班制形式进行教师演示和课堂讨论,另一些教师则要求学生分组学习,自己解决一些问题。在所有教室中,重点是理解标准算法,而不是发明新的策略。在开始授课之前,然后在3-6周的地方价值和加法的授课之后,再加上接受减法指导的2-4周,学生将使用传统的书面技能测验(针对基础概念的专门设计的书面测验)对学生进行评估以及个人访谈。就像这个年轻的学生所期望的那样,预测试成绩很低。例如,完成多位数字加法任务时,169名学生中只有9名正确地重新分组。相反,后期测试的性能始终很高。例如,在169名学生中,有160名正确地重新组合在类似的后测项目上。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基于概念的项目的最高绩效水平,包括访谈中要求学生解释为什么以及如何在多位数算法中进行重组的那些项目。鉴于整个样本中的表现都很高,因此教师实施指导的特定方式(例如,全班演示而不是小组讨论)显然不会显着影响结果。关键似乎是通过连接书面表示形式和物理表示形式来明确关注算法的概念基础。
特征2:学生努力学习重要的数学
我们对有关概念理解教学的文献的解释指出,教学的第二个特征始终如一地促进了学生的概念理解:让学生参与重要数学思想的挣扎或搏斗。与第一个功能不同,第二个功能可能对读者而言并不明显,因此我们首先阐明挣扎的含义,然后阐述挣扎与理解数学之间的理论联系,最后从这个角度回顾一小部分实证研究。
我们用“奋斗”一词来表示学生要花更多的精力来理解数学,弄清楚那些不是立即显而易见的事情。我们不是用斗争来表示无意义的挫折或无理或过分困难的问题所带来的极端挑战。我们并不是说有些材料讲得通的时候,有些学生会感到绝望。我们想到的斗争来自解决难以解决的问题,并解决了可理解但尚未形成的关键数学思想。
杜威(1910,1926,1929)投入了大量精力来阐述这种斗争的过程和后果。 对于杜威来说,斗争的过程对于建立深刻的理解是必不可少的。杜威(1910)说:“这个过程开始了,有些困惑,困惑或怀疑。”随着学生们尝试将事物融合在一起以使其有意义,并找出解决难题的方法,这一过程一直在继续。杜威(1926)指出,传统的学校教学受到媒体的困扰,无法迅速获得答案。这会缩短思考问题的概念方面的机会。杜威(1929)说,对这一主题的深入了解是“将有问题的情况转变为已解决的情况的事业的成果”。
其他认知理论家也发展出类似的论点,将为使主题变得有意义而进行的努力与对主题的更深入的理解相联系。费斯廷格(1957)的认知失调理论发展了认知困惑的概念,将其作为认知增长的主要动力。波多野(1988)以一种更有针对性的方式将认知不一致性视为促进发展表现出概念性理解的推理能力的关键触发因素。对于波多野,认知上的不一致性使学生处于杜威所描述的充满困惑,困惑或怀疑的境地。布朗内尔和西姆塞克(1946)在学校教室中采用了类似的理论结构,将大多数学校任务的重复性与他们认为对增进理解至关重要的过程进行了对比—学生必须感到有必要解决有问题的情况,然后允许他们“糊弄通过”。什么样的任务或问题会带来适当的问题情况?维果斯基(1978)的近端发育区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指导,因为它可以被解释为学生奋斗有可能产生成果的空间。也就是说,在学生近端发育区域的边界附近的新颖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问题,但又提出了足够的挑战,因此有一些新的问题需要解决。
一个伟大的发现解决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但是在解决任何问题上都有很多发现。你的问题可能不大。但是,如果它挑战了你的好奇心并发挥了自己的创造力,并且你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它,那么你可能会经历紧张并享受发现的胜利。
波利亚继续指出,实验和奋斗是发展数学学科必不可少的部分,并建议学生应该体验数学的这一方面以及系统的演绎方面。布朗(1993)明确地将杜威和波利亚的观点与数学斗争的概念结合在一起,布朗将这种现象称为“混乱”。他建议与实际问题作斗争与学生通常会收到的整洁课程大不相同,并且他认为适当的斗争(或困惑)向学生揭示了数学的关键方面。
可以使用较早提出的理解定义之一来表达将斗争与理解联系起来的逻辑,这是本节中感兴趣的学习目标。如果理解被定义为数学事实,思想和程序之间的精神联系,那么奋斗就被视为重新构造这些事物的过程。当无法轻易吸收新信息或发现旧的关系不足以理解新问题时,事实,观念和程序之间的关系就会重新建立。奋斗使人们以更强大的方式重建人际关系。如果将理解定义为参与一个正在变得擅长于做数学和理解数学的人们的社区,那么奋斗就至关重要,因为挣扎可能是社区内个人意义形成的重要方面。这对于数学家的工作至关重要。总而言之,通过识别被假定为发展理解的共同过程,在理解的两种定义中都涉及到与重要数学作斗争。
尽管很少(如果有的话)研究试图隔离和测试斗争对学生概念理解发展的影响,但许多发现表明,某种形式的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406032],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