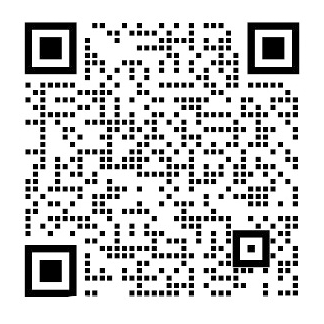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外文翻译
发扬国粹:中国科学社与早期中国数学史研究
作者:胡吉瑞
国籍:捷克
出处:《自然辩证法讯》第38卷第3期
摘要:中国科学社和它的《科学》杂志自从1915年成立,一贯支持中国数学史研究。虽然第一任社长任鸿隽对中国知识遗产怀有轻视态度,但是比他年轻的社员对中国数学史有浓厚的兴趣。桥梁专家茅以升起了尤其关键的作用,先后介绍李俨、钱宝琮到《科学》杂志去发表他们研究成果。《科学》在1915到1939年间发表的中国数学史文章,占了全国这方面的论文的将近20%。科学社之所以跟数学史研究者关系如此密切,可能有以下原因:1)数学史作为现代学科在世界上被建立,成为一种模范,也创造了中国对国际学术贡献的机会。2)1890年代出生的中国科学家希望在国际上提升中国的形象。3)中国传统数学属于“安全的”历史遗产,尤其是跟当时的中医相比。
关键词:中国数学 科学社 李俨 茅以升 钱宝琮
一、导言
1914年6月10日,当任鸿隽(1886-1951)、杨铨(1893-1933)等人决定创办中国科学杂志时,他们希望通过对西方科学的详细普及,传播科学精神。在那个历史性的夜晚,当离开纽约伊萨卡任鸿隽的小房间时,大概没有人认为有必要在他们未来的期刊上用篇幅来研究中国的科学遗产;相反,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迹象表明,这些遗产被认为与“通过科学拯救中国”的目标无关,新的期刊和围绕着它兴起的社会希望与中国的过去保持最坚决的距离,甚至连中国历史上值得被贴上“科学遗产”标签的追求也被否定了。然而,在短短几年内,新的《科学》杂志在中国科学史研究方面的重要性不亚于当时中国的任何一本杂志;仅在中国数学史方面,它就占据了1911年至1940年期间中国数学史总产量的20%。
这种矛盾可能反映出,在期刊的版面上用科学发现的记录和其他喜欢的材料来填满期刊的难度。但是,早期编辑人员对中国科学史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使中国科学史(尤其是中国数学史)成为推动中国现代科学研究的一部分。此外,数学史本身就被认为是一门现代科学学科,中国人可以通过对其遗产的调查,对其做出宝贵的贡献。
在本文中,我将首先分析南宋早期领导人对科学史尤其是中国科学遗产的态度。在接下来的部分,我将展示《科学》杂志在民国时期中国数学史学中的重要作用。最后,我将讨论关于上述悖论的一些假设:为什么在SSC为创建中国科学文化所做的努力中,中国数学史被认为是有用的,尽管最初对史学研究持不屑一顾的态度,认为它分散了真正彻底的现代化的注意力,但中国数学史却被接受为有用的?
二、《科学》与中国科技遗产
科学会,后改名为中国科学会,成为民国时期(1911-1949年)最重要的科学和更广泛的科学文化的推动者。它是由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创办的,严格意义上说,最初是以出版期刊为目的,虽然它的规模逐渐扩大,并在迁往中国后与政治势力的关系更加密切,但它的期刊《科学》仍然是其活动的中心。
1914年,康奈尔大学的中国学生创办了《科学》杂志,他们有几个目标和目的。其中一个目的是要反击对中国传统的内向兴趣,因为中国传统的内向兴趣过去和现在仍然是中国近代化的拖累,而现在的科学新闻和关于真正的西方科学、其发现和发展的开阔眼界的事实,则是对中国传统的内向兴趣。任鸿隽是辛亥革命的元老,也是SSC较为年轻的创始人中的权威人物。他坚信“吾国学术思想之历史,一退化之历史也”[7],而那些“自鸣得意者” (扬己者),为了“显示我们的传统力量,压抑别人的辉煌”,才提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近代科学见解,以“明吾国固有之长,而抑他人矜饰之焰”,却忽略了这些零散的成就并不具备科学的系统性。此外,任鸿隽在1916年10月第二次南宋史学会年会上的讲话中,对古典史学和文艺学(经史子集之学)的评价是:“专以钻研陈言为务,即有所得,不过古人之糟粕,以钻研陈言为务,即有所得,不过古人之糟粕”[9]。任鸿隽等人清楚地看到SSC的使命是鼓励生产出与中国以往不同的新知识。
中国科协和科协的创会文件和纲领性文件对中国科学史只字未提。他们把科学史和科学家传记作为《科学》要发表的第四类文章[2],但这些文章都是含蓄地针对西方科学,特别是近代科学的研究。任鸿隽在《科学》创刊号的开篇,就以“中国没有科学”[7]为例,而后世著名的昆虫学家秉志(1886-1965年)在其《古今著名生物学家调查》[1]中更巧妙地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其中列举了普林尼、盖伦、维萨柳斯等人,但没有中国近代以前的作者。科学史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在中国读者中广泛使用的宣传科学的手段。即使是关于近代发现的文章,也往往是以年谱的形式,按时间顺序编排。任鸿隽尽管不喜欢 “翻阅旧文”,但他对史学史却情有独钟,以至于他在1916年第二届科学史学会年会的主要报告被称为“外国科学会及本会史”。任鸿隽甚至把SSC的成立当作历史来介绍,一扫而过,认为SSC成立仅两年多的事实。“谁知道我们学会的这两三年的历史,是不是我们学会辉煌的两三百年历史的开端呢?”[8]普遍采用的进化论观,以及更传统的学者倾向于将历史作为合法性的来源,使得历史记述成为建立科学学科合法性的关键。但中国科学并不是这些说教性文章的有效成分。在SSC创始人中最有成就的数学家胡明夫,在他对数学的不同分支的论述中,显然从未将中国数学纳入其中,不得不说,这些论述都是以最近的发展为中心。
如果我们调查一下《科学》的前四卷,在SSC在美国时全部或部分出版的《科学》,我们发现共有七篇文章专门介绍中国的科学,其中一篇是任鸿隽在第一期中已经提到的著名文章,解释中国没有产生任何值得称道的科学。其他的文章还有六篇。
这项调查显示,虽然有前苏联科学史研究会成员对中国科学史有浓厚的兴趣(胡适和后来以批评胡适“文学革命”而闻名的植物学家胡先骕都是如此),但大多数人都是在西方科技史中发现了与中国有关的资料后,才开始涉猎的。桥梁建设者茅以升(1896-1989)的《桥梁建设者》一丝不苟地研究和取材也是如此。
后期杂志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逐渐升温,到1926年出版的《中国科学史资料来源》(第11卷第6期)专刊,达到了高潮。中国数学史在这次SSC对中国科学史的开放中,中国数学史占据了突出地位。反之亦然,SSC期刊和部分社员在中国数学史的建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李俨和中国数学史进入《科学》的历程
茅以升的《中国pi;史简史》一文中,向读者介绍了毛泽东的同学李俨(1892-1963),25岁时已是一位阅读量很大、意志坚定的中国数学史家。李俨后来成为中国科学史界的重要人物,从30年代起出版了多部著作,并与美国、英国、日本、苏联等国的著名科学史学家进行了交流。1947年,他对中国科学史学会和《科学》对其学术分支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中国科学会从民国初年起,就组织了各种科学研究,出版了《科学》杂志。中国数学的研究也是在同一时期开始的。”[3]这一评价,从民国时期中国数学史上的出版物调查中可以看出,SSC及其杂志的重要性。
李俨不是留学生,由于辛亥革命的影响,失去了家庭的经济支持,父亲也因辛亥革命的失败,不得不放弃了在唐山工科学校的学习,转而投身于陇海铁路的建设,最终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但在唐山的两年(1913-15年),他在唐山的两年时间里,与SSC的创始人建立了联系。他的同学包括未来的SSC的领导人杨泉和稍年轻的毛益生,他对李俨的学识非常佩服,在1916年进入康奈尔大学并加入SSC后,他一直保持着联系[11]。李俨最终也加入了SSC,并在1930年以三年内交纳100银元的承诺,获得了 '永久社友 '的身份[11]。在他在中国西北建设陇海线西段的漫长岁月里,他是那里为数不多的活跃的SSC会员之一。
四、钱宝琮与数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沿革
我们可能会想把李俨在科学中的成功解释为他与SSC的特定成员的良好关系,但是,用近代风格书写的中国数学社会与历史的亲和力更深。与任鸿隽那一代的激进分子不同,19世纪90年代出生的年轻成员同样渴望将现代科学和文化带入中国,为中国赢得外国同行的认可。传统的中国数学,尤其是对于新式教育精英中的众多工程师来说,是一个明显的候选者。他们接受了大学阶段的数学教育,提高了对数学知识的历史积淀的认识,对不同数学家的贡献大于初等数学的认识。这一代中国数学史上下一位著名的数学家钱宝琮(1892-1974)也是一位工程师。
钱宝琮曾在伯明翰和曼彻斯特学习工科,回国后在中学和后来的大专院校教数学。他在1919年加入了SSC(《中国科学社记事》191919:1030),但作为SSC的成员并不特别活跃。当时,他对中国传统数学的兴趣还是纯粹的业余爱好者[6]。后来,他才开始更认真地研究,1921年在《科学》(第4卷第1期:1-10)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九章问题的分类》,很快又有三篇文章在同卷上发表。他在《科学》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1923年的《中国数学书中的pi;的研究》[5]。这篇文章的序言是由茅以升写的,因此,他可以说是把中国数学史上的两位主要的数学史家都引到了史学界的注意。毛泽东回忆起他早年的同题文章,谦虚地指出了文章中的许多错误和不准确之处。毛泽东的序言,可以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数学及其研究的辩护,也可以看作是对西学派的怀疑。
圆周率的研究,是我国数学中可以与西方争光的部分之一。然而近年来,人们对西方数学的关注出现了偏差,前辈们的伟大成就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亟待准确记录、揭示和评价,以弘扬国粹[5]。
钱宝琮和李俨最终都成为了《科学》的编委会成员。其他SSC成员也为中国数学史做出了贡献,只是规模较小。朱文鑫(1883-1939),1919年2月26日在上海加入SSC,主要是天文学家,但除了中国天文学史外,还写过中学数学史。傅种孙、黄际遇等数学家和SSC的早期成员,也偶尔写过中国数学史。尽管有这种多样性,但必须强调的是,在500多页的《中国数学史》中,几乎所有关于中国数学史的克己学著作都是由李俨或钱宝琮撰写的。
五、为什么数学史和SSC于对方都很重要?
鉴于SSC的创办者对民族传统的吹嘘持谨慎态度,而又急于推广现代科学,《科学》为何会成为中国数学史上的主要出版渠道?对于这个悖论,有几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有些是针对20世纪10年代末和20世纪20年代SSC的情况,另一些则揭示了20世纪初中国更广泛的困境。
人们不得不把钱宝琮和李俨的个性和他们对中国数学史学的研究方法作为具体的历史偶然性来对待。这需要一种奇特的心态和巨大的决心,要用大半生的时间去梳理中国古代的数学典籍,以确立精确的事实。而在这些特殊的思想中,有一个人(李俨)在两年的高等教育期间,遇到了未来的SSC核心成员杨泉和毛益生,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巧合;正是后者,也因为他自己对中国数学的兴趣,建立了这两位历史学者与中国科学界的联系。
另一方面,即使撇开现有作者的博学和生产力等因素,《中国数学史》也有几个特点,使其对期刊编辑和SSC的目标具有吸引力。即使有些SSC的领导人对“民族自豪感”、“国粹”以及这些名词所携带的包袱很敏感,但他们也认识到,中国科学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需要将国外的方法与国内的问题和材料相结合。植物学和地质学如此,工程学如此,一般的科学讨论也是如此。李俨和钱宝琮的《数学史》就是试图将西方的科学方法应用到中国的材料中,并追赶日本和欧美的类似活动。
1927年至1934年是中国传统医学出版的高峰期,这是个有趣的巧合,因为1927年至1934年是中国传统医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医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试图禁止传统医学的尝试失败的时期。新兴的科学机构大多反对传统医学,没有任何关于中医历史的论述出现在《科学》上。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的数学是一个相对一致的话题。传统算学的实践已经被现代的方法安全地取代,当时并没有人努力恢复传统,把它作为现代性传播的可能障碍。在现代科学时代,对中国数学的历史研究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颂扬中国传统的形式。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关于民国初年的数学史家们,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他们的背景。他们属于转型期的一代人,接受过一些初级的古典教育,但在1902-3年后进入近代学校学习,有时在美国或欧洲学习。无论是《科学》还是那个时期的其他期刊,都没有显示出早期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数学史上的活动,他们并不缺乏接触过中国传统数学的人。在近代学校学习近代学科的共同经验和“通过科学救中国”的共同愿景和希望,是这一过渡时期的典型代表人物,这使得他们的同事们更容易接受李、钱的中国数学史,将其作为一种有利于中国近代科学建立的正当追求。
科学家与数学史家之间的共生关系一直持续到专业化程度和新的的提高,甚至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代科学家的出现,使中国科学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此后,数学史和科学期刊都在抗日战争的冲击下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数学史和科学期刊又迎来了新的发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英语原文共 8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68543],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