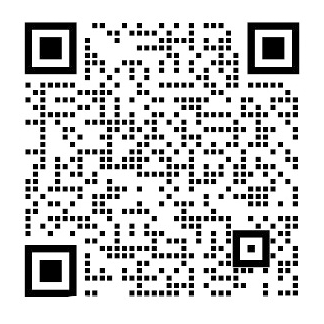The project of pursuing workplace equity has reached a new stage. Racial and gender inequality persists in many places of employment.However, the explanations and solutions for these conditions have become more complex and elusive. Many employers now have formal policies prohibiting race and sex discrimination, and procedures to enforce those policies. Cognitive bias, structures of decisionmaking, and patterns of interaction have replaced deliberate racism and sexism as the frontier of much continued inequality.
Frequently, sexual harassment and discriminatory exclusion involve issues that depart from the 'first generation' patterns of bias. Unequal treatment may result from cognitive or unconscious bias, rather than deliberate, intentional exclusion. 'Second generation' claims involve social practices and patterns of interaction among groups within the workplace that, over time, exclude nondominant groups. Exclusion is frequently difficult to trace directly to intentional, discrete actions of particular actors, and may sometimes be visible only in the aggregate. Structures of decisionmaking, opportunity, and power fail to surface these patterns of exclusion, and themselves produce differential access and opportunity.
Thus, second generation manifestations of workplace bias are structural, relational, and situational. The underlying problems are exacerbated in workplaces with flexible, decentralized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at require workers to participate more actively in decisionmaking concerning work assignments, leadership, advancement, pay, and evalua-tion. In response to market and technological pressures for adaptability, flexibilit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se emerging organizational forms eschew stability, permanence, and rule-driven decisionmaking. In these environments, however, interactions that produce the occasions for exclusion are simultaneously frequent and organizationally necessary. The complex and dynamic problems inherent in second generation discrimination cases pose a serious challenge for a first generation system that relies solely on courts (or other external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to articulate and enforce specific, across-the-board rules. Any rule broad enough to cover the variety of contexts and conduct that might arise will inevitably be quite general and ambiguous, and it will produce considerable uncertainty about the boundaries of lawful conduct. Ambiguous rules will provide inadequate guidance to shape conduct, and will undermine efforts at anticipatory compliance. This uncertainty in turn tends to induce gestures of compliance with the legal norm, without necessarily inducing any change in the underlying behavior causing the problem.Employers fear of sanctions if internal evaluation reveals previously unrecognized bias has the perverse effect of discouraging them from inquiring into or addressing second generation problems.
Efforts to reduce the uncertainty of general and ambiguous legal norms by articulating more specific and detailed rules produce a different but equally problematic result. Specific commands will not neatly adapt to variable and fluid contexts. Inevitably, they will be underinclusive, overinclusive, or both. Moreover,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effective remedies for second generation bias is inseparably linked to that of defining the nature of the problem itself. Separating problem definition from its institutional context undermines the efficacy of the resulting legal norm as well as the remedy designed to achieve it. Notwithstanding the limitations of solving problems involving complex relationships through specific commands, much of the current debate over sexual harassment and discrimination revolves around identifying the best theory of what constitutes discrimination. This court-centered regulatory focus is understandable, given the judiciarys historic preeminence in the articul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antidiscrimination norms. However, this focus now obscures a deeper innovation inchoate in the emerging regulatory approach to the problems of sexual harassment and the glass ceiling.
Over the last decade, an interesting and complex regulatory pattern has emerged. Multiple public, private, and nongovernmental actors are actively and interactively developing systems to address sexual harassment, glass ceiling, and other second generation problems. Each of these institutional actors has begun to approach these questions as posing essentially issues of problem solving. Each has, to varying degrees, linked its anti-bias efforts with the more general challenge of enhancing institutional capacity to manage complex workplace relationships. These multiple actors have, perhaps unwittingly, begun to carve out distinctive roles and relationships that form the outlines of a dynamic regulatory system for addressing second generation discrimination.
This Article offers a framework that makes visible these emerging and converging patterns of response to second generation discrimination. It explores the potential for a de-centered, holistic, and dynamic approach to these more structural forms of bias. This regulatory approach shifts the emphasis away from primary reliance on after-the-fact enforcement of centrally defined, specific commands. Instead, normative elaboration occurs through a fluid,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blem solving and problem definition within specific workplaces and inmultiple other arena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judiciary. In this framework, compliance is achieved through, and evaluated in relation to,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capacity to identify, prevent, and redress exclusion, bias, and abuse. This approach expands the field of 'regulatory' participants to include the long-neglected activities of legal actors within workplaces and significant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such as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insurance companies, brokers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追求工作场所平等的项目已经到了新的阶段。种族和性别不平等在许多就业场合依然存在,但这些条件的解释和解决方案变得越来越复杂和难以捉摸。许多雇主现在都有禁止种族和性别歧视的正式政策以及执行这些政策的程序。认知偏见,决策结构和互动模式已经将蓄意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取代为持续不平等的前沿。
性骚扰和歧视性排斥常常涉及偏离“第一代”偏见模式的问题。不平等的治疗可能是认知或无意识的偏见,而不是蓄意的,有意的排斥。 “第二代”主张涉及社区实践和工作场所群体之间的互动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排除非优势群体。排除往往很难直接追踪到特定行为者的有意,独立的行为,有时候只能在总体上可见。决策,机会和权力的结构不能表现出这些排斥模式,而且自身也产生不同的获取和机会。
因此,工作场所偏见的第二代表现是结构性,关系性和情境性。在具有灵活,权力下放的治理结构的工作场所中,潜在的问题更加严重,这要求工人更积极地参与关于工作任务,领导,进步,薪酬和评估的决策。针对适应性,灵活性和技术创新的市场和技术压力,这些新兴的组织形式避开了稳定性,持久性和规则驱动型决策。然而,在这些环境中,产生排除场合的互动同时是频繁和组织上必要的。
第二代歧视案件所固有的复杂和动态问题对于仅依靠法院(或其他外部政府机构)来表达和执行具体的全面规则的第一代系统构成严重挑战。足以涵盖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和行为的任何规则都将不可避免地是相当普遍和不明确的,并将对合法行为的界限产生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不明确的规则将为制定行为提供不足的指导,并将破坏预期遵守的努力。这种不确定性往往会导致遵守法律规范的手段,而不一定会引起导致问题的潜在行为的任何变化。
如果内部评估揭示以前未被承认的偏见,雇主对制裁的恐惧具有阻止他们进行查询的不利影响或解决第二代问题通过阐明更具体和详细的规则,努力减少一般和模糊的法律规范的不确定性产生了不同但同样成问题的结果。具体命令不会整齐地适应变量和流体上下文。不可避免地,他们将是不够独立的,过分的或两者兼而有之。此外,设计和实施有效补救第二代偏见的过程与确定问题本身性质的过程密不可分。将问题定义与制度背景区分开来,会破坏所产生的法律规范的效力以及旨在实现这一点的补救办法。
尽管通过具体指令解决涉及复杂关系的问题有限,但目前关于性骚扰和歧视的大部分辩论都围绕着确定什么是歧视的最佳理论。鉴于司法机构在阐明和执行反歧视规范方面的历史性优势,以法院为中心的监管重点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一焦点现在掩盖了对于性骚扰和玻璃天花板问题的新兴监管手段的深刻创新。
在过去十年中,出现了一个有趣和复杂的监管模式。多个公共,私人和非政府行为者积极和互动地发展系统,以解决性骚扰,玻璃天花板和其他第二代问题。这些制度行动者中的每一个已经开始将这些问题看作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问题。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将其反偏倚工作与提高机构能力以管理复杂的工作关系的更为普遍的挑战相联系。这些多个行为者也许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形成独特的角色和关系,形成了处理第二代歧视的动态监管体系的纲要。
本文提供了一个框架,可以看出这些新兴和趋同的对第二代歧视的反应模式。它探讨了对这些更具结构性的偏见的偏心,整体和动态的方法的潜力。这种监管方法将重点从主要依赖于集中定义的特定命令的事后执行转移。相反,规范性阐述是通过在特定工作场所和多个其他领域的问题解决和问题定义之间的流动,互动的关系发生的,包括但不限于司法机构。在这一框架下,通过改善机构能力来确定,预防和纠正排斥,偏见和滥用行为,并通过评估来实现遵守。这种方法扩大了“监管”参与者的领域,将工作场所和重要非政府组织(如专业协会,保险公司,经纪人,研究联盟和倡导团体)中长期被忽视的法律行为者的活动纳入其中。这些行动者已经开始在汇集信息,制定有效性标准和评估当地解决问题努力的适当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种第二代监管方式的主题是结构主义。这就是说,我的意思是鼓励发展机构和程序来制定特定情况下的一般规范。信息收集,问题识别,补救和评估的互动过程中出现了“合法性”。规范促进了动态互动,跨越既定的概念,专业和组织边界,以反映观察到的问题。这种方法鼓励在信息收集,组织设计,激励结构,有效性措施和将责任制度化的方法方面进行实验,作为明确的法律法规体系的一部分。影响工作场所实践的工作场所和非政府机构在本监管制度中被视为立法机构,而不仅仅是国家或市场监管的对象。法院,雇主和非政府行为者在促进结构主义转变中发挥重要作用。最近最高法院的裁决可以 - 我不要说必须阅读鼓励提供情境规范制定和解决问题的工作场所结构。
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情况已经与更具结构性和动态导向的第二代偏见方法相融合在工作场所也。一些雇主通过重新设计他们的决策,工作分配和解决冲突的制度来应对偏见,排斥,营业额和玻璃上限的模式,以同时解决对公平和效力的担忧。其他多种场合,包括但不限于司法机构。在这一框架下,通过改善机构能力来确定,预防和纠正排斥,偏见和滥用行为,并通过评估来实现遵守。这种方法扩大了“监管”参与者的领域,将工作场所和重要非政府组织(如专业协会,保险公司,经纪人,研究联盟和倡导团体)中长期被忽视的法律行为者的活动纳入其中。这些行动者已经开始在汇集信息,制定有效性标准和评估当地解决问题努力的适当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种第二代监管方式的主题是结构主义。这就是说,我的意思是鼓励发展机构和程序来制定特定情况下的一般规范。信息收集,问题识别,补救和评估的互动过程中出现了“合法性”。规范促进了动态互动,跨越既定的概念,专业和组织边界,以反映观察到的问题。这种方法鼓励在信息收集,组织设计,激励结构,有效性措施和将责任制度化的方法方面进行实验,作为明确的法律法规体系的一部分。影响工作场所实践的工作场所和非政府机构在本监管制度中被视为立法机构,而不仅仅是国家或市场监管的对象。
法院,雇主和非政府行为者在促进结构主义转变中发挥重要作用。最近最高法院的裁决可以 - 我不要说必须阅读,鼓励提供语境规范制定和解决问题的工作场所结构。至少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案例也与更为结构化和动态导向的方法融合在工作场所内的第二代偏见之中。一些雇主通过重新设计他们的决策,工作分配和解决冲突的制度来应对偏见,排斥,营业额和玻璃上限的模式,以同时解决对公平和效力的担忧。性骚扰和玻璃天花板法则鼓励和加强了内部解决问题和争端解决过程的广泛的组织发展。本文研究了三家建立内部流程追求法律规范的公司,同时提高了组织处理涉及复杂关系的更广泛问题的能力。它还描述了在工作场所内和跨越工作场所运作的中间行为者,已经成为执行工作场所创新以解决偏见的重要角色。这些非政府行为者同时影响有效的工作场所问题解决的司法定义,并将法律规范转化为组织制度和标准.它借鉴了三个案例研究,以勾勒出建立在合法性和问责制中的第二代偏见的方法,然后描述法律在鼓励内部解决问题系统的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部分探讨了中间人在经纪司法制定与工作场所创新之间的关系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第四部分描述了法律和实践中抵制结构性行为的反倾销趋势,以及需要开发分层和互动的“监管”框架,破坏这些倾向,并鼓励有效的解决问题。 最后一部分提出了将组织边界内部和跨组织边界之间的关系制度化的建议,并提供必要的问责制和基于情境的思考。 最后一部分也考虑了对这种整体监管方式的潜在反对意见,以及对法律和律师作用的影响。
第一代就业歧视案件反映了导致通过民权立法的社会和政治条件。通过公开排斥,就业机会隔离和有意识的定型观念维护了工作场所隔离。主导的个人和团体故意排除或次要的女人和人的色彩。与性别或种族高度相关的工作要求,如教育和培训先决条件,身高和体重要求,“巩固了这些排斥模式。因此,第一代案例主要侧重于处理长期结构隔离的后果。在第七章通过之后,许多公司已经消除了明确的排斥政策,但继续采取排他性做法。这些做法虽然嵌入到排斥结构中,但往往是显而易见的,普遍的,符合一个很好理解的歧视思想。排斥模式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追溯到从事蓄意排斥形式的个人或团体的行为。这些更公然的做法避免了发现和分析更为微妙的偏见形式的必要性,即使在民权法初期阶段也是如此,这种偏见也是有种族和性别边缘化的。第一代歧视的“错误”围绕着基于种族或性别的故意排除或从属。这种不平等待遇的形式违反了公正和正式平等的明确无争议的规范。这种反歧视原则的前提是,根据定义,种族或性别与工作的能力无关,而且考虑种族或性别本质上是任意的,诋毁的和不公平的。第一代的影响案例类型也从故意排斥的前一代衍生出他们的道德叮咬和合法性,尽管他们从来不适合整体地反映在主导的反歧视范式中。歧视性申请程序和测试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使过去的故意,系统排除的模式持续存在,或反映了持续的,尽管没有明确的,有意的排斥。第一代问题的补救措施共享了这些清晰,均匀和简单的特点。补救办法经常采取规则的形式:在招聘或晋升决定中停止考虑种族或性别;根据他们的性别或种族向以前排除的人提供回报;为所有工作人员提供相同的机会,标准和进程,无论种族或性别如何,获得,培训,雇用和晋升;一般向公众传播,特别是公司不歧视的颜色社区;采取措施增加以前被排斥群体求职的兴趣;采取目标来整合以前分离的工作;停止使用歧视性测试。这些补救措施禁止不平等待遇,通过结果目标来排除工作场所,增加申请人群体中妇女和人群的代表性,消除显然排斥性而不是与工作有关的检验或标准。但是,审查员直接鼓励修改组织内文化和决策过程,从而纠正偏见,陈规定型观念和不平等的访问。
第一代歧视并没有消失,而且在最近针对德士古公司和三菱等公司的诉讼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该公司没有制定强有力的方案来解决甚至公开的偏见。然而,这种歧视往往是串联的与微妙,互动和结构性偏见取代或取代。事实上,即使在民权时代的早期阶段,第二代偏见往往与第一代偏见并存。但是,公开和熟悉的排斥形式的存在避免了更深入探讨的需要,至少作为监管问题,微妙形式的偏见的意义。因此,第一代补救办法往往不侧重于与更明显和公然的排斥形式一起运作的偏见的组织和文化层面。因此,术语“第二代”最准确地指的是一种微妙而复杂的偏见形式及其适当的监管反应,而不是偏向动力学的时间顺序发展。第二代索赔经常涉及工作场所各组织之间的互动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排除非优势群体。这种排除很难直接追溯到特定行为者的有意,独立的行为。例如,现在常见的骚扰类型的索赔目标是同僚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有权排除或排斥同事,但可能缺乏正式的雇用,纪律或重新分配权力。这种形式的骚扰可能包括破坏妇女的认知能力,将其从关键的社会互动中解脱出来,或者制定违反定型观念的性别或性取向的行为。这是特别困难的,因为行为参与者可能会以相同的方式感受到相同的行为。此外,当被认为是孤立的时候,出现性别中立的行为可能在与更广泛的排他性模式相联系时可能产生性别偏见。特定行为的社会影响可能因其发生的背景和组织文化塑造各种参与者的看法而有所不同。在边缘地区,歧视性骚扰与合法的,尽管不专业的破坏性行为之间可能难以划分。在主观就业实践中涉及的偏见主张的性质也发生了类似的演变。排除越来越多的结果不是从正式的意图努力排除,而是作为由日常决策和工作场所关系的结构形成的正在进行的交互的副产品。玻璃天花板仍然是妇女和人们的色彩的障碍,主要是因为互动,非正式规范,网络,培训,指导和评估的模式,以及没有系统的努力来解决这些模式产生的偏见。工作场所的环境,排斥性的主观就业习惯和玻璃天花板本质上是复杂的。他们的复杂性在于伤害的多重观念和原因,伤害的互动和情境特征,合法与不法行为之间的边界模糊,以及有效补救的结构和互动要求。这种复杂性通过全面的相对具体的命令和事后执行机制来抵抗定义和解决。这些特征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最好地说明。考虑一个大型律师事务所,投诉涉及一系列性别问题。该公司的几乎一半的员工是女性,但女性的代表人数在高级副员/初级合作伙伴级别急剧下降。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几乎完全是男性。几个公司部门,如税收和兼并收购,妇女人数非常少。这家公司的律师“全天候工作”,经常在大型复杂案件上合作。对于许多律师来说,律师事务所既是专业人士,也是社会团体。关于人事问题的决策主要是主观和酌处权,对其效力或公平性几乎没有系统评估。取决于关于案件转让,获得培训和接触重要客户的非正式决定。对专业成功也至关重要的新律师的指导模糊了个人和专业互动之间的界限。一群妇女质疑最近的拒绝妇女促进伙伴关系的决定,该公司一般不能保留和促进妇女,尽管有相当的入学资格,还有一系列个人事件引发了性骚扰和性别偏见的投诉。部分原因是公司在入门级别积极招募妇女,不能追踪工作分配和晋升方式,直到这些投诉出现之前,该公司的管理层基本上没有意识到任何问题。这些投诉涉及一系列问题:男女工作分配模式和培训机会的差异;合作伙伴对性别化工作环境的宽容,否则他们是重要的“造雨者”;男性律师,特别是主要是男性部门对妇女的外貌,性别和能力的例行评论;对性别定型观念对妇女能力和工作作风的严格评估;避免某些部门成员与妇女接触工作;对妇女的表现进行过度审查,以及妇女对别人的贡献的隐形。这些投诉与不同工作团队的士气低下和生产力的担忧相吻合。经过审查,该公司发现公司中男女保留率和晋升率存在显着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描述的偏见问题是由组织文化形成的互动模式所导致的。这些相互作用影响工作场所的条件,获取和随着时间推移的机会,从而构成包容或排斥的结构。他们不能仅仅追溯到一个“坏演员”的性别歧视。也不能通过将问题分解为离散的法律索赔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在背景下和与更广泛的行为和获取方式相关的情况下,才能明白这一行为的整体性别影响。没有对这些模式进行有系统的体制性反思,以及对工作场所条件,获取机会和进步机会的影响,有助于其累积效应。整体组织文化影响特定行为在某一特定工作场所产生偏见的程度。与性别隔离和边缘化结合发生的意见或行为可能是歧视性的,而相同的陈述可能在更综合的情况下几乎不产生性别排斥。此外,这些互动的参与者可能会有相同的行为,具体取决于他们在行为,权力,性别,流动性,支持网络以及跨性别互动程度方面的立场。那些参与制造偏见的行为可能不会将他们的行为视为有问题或歧视性的。鉴于组织倾向避免解决冲突或工作场所的相互作用问题,许多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根本没有被要求解释工作场所关系的任何方面,直到实际出现歧视投诉。此外,组织对骚扰或排斥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483657],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以上是毕业论文外文翻译,课题毕业论文、任务书、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
您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 晚年丧偶和已婚妇女的休闲活动和抑郁症状外文翻译资料
- 认知行为与心理动力人际治疗对进食障碍的影响:一项关于缓解期患者特征和改变在进食障碍特异性和一般精神病理学中的作用的荟萃分析外文翻译资料
- 社区和疗养院里老年人的精神需要外文翻译资料
- 日本社区协会的参与和正式志愿者外文翻译资料
- 社会工作组织中的变革型领导与社会工作者更替的关系外文翻译资料
- 社区参与现实世界:新形势下的机遇与陷阱治理空间外文翻译资料
- 提升在社区独立生活的长者的生活满意度:看护者对志愿者的看法外文翻译资料
- 非典型就业群体失业保障制度的研究外文翻译资料
- 日本长期护理保险和综合护理外文翻译资料
- 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并轨研究外文翻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