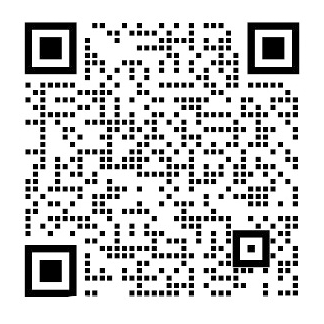Democracy and the Grassroots Sector in Singapore
In independent Singapore, the extensive grassroots sector has been linked with party-political interests. The Peoplersquo;s Action Party has relied on it for mass mobilisation and surveillance. Since the mid 1980s,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demands of the new economy and rising pressures for state welfare have been compelling reasons to evolve an open, consultative and participative culture. The developmentalist government regards an apolitical lsquo;civicrsquo; society—not a politically antagonistic lsquo;civilrsquo; society—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generating such a climate. The newly appointed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uncils—local administration units in the PAP-controlled grassroots sector—can be read as a means of reducing the political risks of growing an increasingly necessary lsquo;people sectorrsquo;.
The Grassroots Sector as a Barrier to Liberal Democratisation
Liberal conceptions of democracy demand that citizens be treated as rational and autonomous rights-bearing individuals at liberty to devise, pursue and revise their own life-choices, and to associate freely in a plural civil society, all within an environment that protects them from each other and from the state whose purpose should not proceed beyond maintaining such an environment. Where political elections are concerned, there must be the real possibility of parties in government losing their position to other par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nlightened and unobstructed will of the majority. Governments are therefore forbidden to adopt unfair strategies simply to keep themselves in power. By these stringent standards that are rarely simple to apply in practice, Singaporersquo;s political system fails on a number of counts, even though the governmentrsquo;s political rhetoric has since the mid 1980s embraced more determinedly the value of openness, consultation and participation for reasons,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other than democracy and liberal ideals perse.
The main apolitical grassroots organisations fall directly under the Peoplersquo;s Association, a statutory board chaired by the Prime Minister himself and associated administratively with the 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Sports. The government has nearly always initiated and helped to sponsor and fund many of the major grassroots projects, activities and programmes. Secondly, most of the grassroots committees are chaired or advised by PAP MPs or prospective MPs. Other grassroots leaders are not meaningfully elected, are mainly PAP appointees and occupy their positions for very long terms. Thirdly, membership of the different grassroots committees often overlaps, with top grassroots leaders simultaneously serving actively on various committees and therefore stabilising the grassroots sector and preventing members from taking independent and potentially antagonistic action. Fourthly, the functions of the different grassroots committees overlap in practice so that the likelihood of any section of the grassroots lsquo;going astrayrsquo; is quite minimal.
Another broad reason for characterising the grassroots sector as a barrier to liberal democracy lies in its largely conservative outlook and suspicious views about change. The more traditional grassroots sector is entrenched in many well-established procedures devised during the more turbulent decades of independence, in the chain of hierarchical and even patronal relationships, and in the ontological security drawn from a singular sense of mission. The grassroots sector has been carved out as a space reserved for the traditional, non-meritocratic, non-technocratic eacute;lite. As long as liberal democracy introduces into this space the element of open competition for power, recognition and patronage, it will remain the object of suspicion.
Limited Pressures for Liberal Democratisation
Although the grassroots sector has been propped up as a PAP bulwark against pressures for liberal democracy, in reality these pressures have been limited. Risk-averse Singaporeans have generally been more interested in material acquisition, in the pursuit of personal success and enjoyment and in maximising the chances of securing these through a government that has had a long, well-documented and exclusive record of successfully delivering the goods. Ordinary Singaporeans may want more opposition parliamentarians to check against governmental abuse, but not a different party in government (Vasil, 1993, p. 303).
The unexpected election to Parliament of an opposition candidate in the 1981 by-elections and then a second one in the 1984 general elections broke the PAPrsquo;s absolute parliamentary monopoly held since 1968. By the 1991 general elections, four opposition MPs won seats, but this figure has dropped to two since the general elections in 1997. No drastic electoral swings are expected in the near future as the PAP continues to employ superior electoral strategies in the context of several structural advantages. These derive from political incumbency and effective influence over the organs of state and mass media, an electoral system that is based on the first-past-the-post principle and multimember constituencies, effective parliamentary control over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and an entrenched ideological hegemony configured to favour PAP rule. Nonetheless, the doomed fates of many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responsible at some time or other for great economic success in and out of Asia must give the PAP government some cause for concern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a long-term buildup and intensification of democratic pressures. This is especially sobering in the context of shorter business cycles bringing severe economic crises that threaten political legitimacy.
Many influential elements in the West, including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operating in Asia, global research institutes, neo-conservatives and communitarians, hold quite a high regard for various aspects of the kind of soc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新加坡的民主和基层部门
在独立的新加坡,广泛的基层部门已经与政党利益紧密相连。人民行动党一直依靠它来进行群众动员和监督。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新经济的日益复杂的需求和提高国家福利的压力已经成为寻求一个开放的、协商和参与文化的迫切理由。发展主义的政府把一个非政治化的“公民”社会,而不是一个政治化的敌对“公民”社会,视为其生成发展的重要手段。新任命的社区发展委员会是在压力控制下的基层政府的联合,它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减少在发展一个日趋完善的“人民部门”中日益增长的政治风险的途径。
基层部门是自由民主化的一个障碍
自由民主的观念要求公民被视为理性和自主的权力分担个体,自由地去制定、追求和改变自己的人生选择,并且在一个多元的公民社会里自由地联合在一起,所有处在这种大环境下的公民的自由都不受到来自他人的伤害,也不受来自国家的干涉,国家为了维持这种社会环境不能强制推行它的意图。在政治选举中,存在着一些真实的可能性,政府的政党在与那些与大多数人开明、畅通的意愿相契合的政党的较量中,会失去其政治地位。政府因此被禁止采取不公平的策略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这些严格的标准,很少是简单的应用在实践中,通过这些标准,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在许多方面失败,即使政府的政治言论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更坚决地去迎合开放,协商和政治参与的价值观,重要的是要注意,除了民主和自由主义思想本身以外。
一些主要的非政治化的基层部门直接出于人民协会之下,法定董事会由总理本人和相关管理与社区发展和体育协会主持。政府几乎总是发起并帮助去赞助许多主要的基层项目,活动和项目。其次,大多数基层委员会由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或未来的国会议员主持或建议。其他基层领导人没有当选,主要是因为人民行动党任命并占领他们的位置很长时间。第三,不同的基层委员会的成员经常重叠,同时与基层高层领导人积极在各种委员会服务,因此稳定基层部门和防止成员采取独立的和潜在的敌对行动。第四,在实践中不同的基层委员会的职能重叠,这样基层的任何部门“迷路”的可能性最小。
将基层部门描述成自由民主障碍的另一个普遍的原因主要在于它对于改革的保守估计和怀疑态度。在更加动荡的几十年独立期间,更加传统的基层部门植根于许多程序设计完善过程中,存在于层次链甚至互助的关系中,并且存在于从一个单个的使命感中延伸出的本体论。基层部门已经被作为一种保留传统、非精英、非技术官僚精英的空间而独立出来。只要自由民主介绍到这个空间,成为开放竞争的力量,承认和保护,这将保持怀疑的对象。
自由民主化的有限压力
虽然基层部门已经成为了抵御自由民主压力的人民行动党的堡垒,但实际上这些压力都是有限的。规避风险的新加坡人对物资筹措更感兴趣,在追求个人成功和享受,并通过长时期,证据充分的和已成功交付货物的排他记录的政府来最大限度地确保这些的机会。一般新加坡人可能需要更多的反对派议员监督政府权力滥用,而不是在政府体系里的不同政党(瓦西里,1993年,第303页)。
意想不到的反对党候选人在1981年的选举议会补选,然后第二个1984年的大选打破人民行动党自1968年以来举行的议会绝对垄断。1991年大选,四个反对党议员赢得席位,但这个数字自1997年大选已经下降到两个。没有激烈的选举波动预计着在不久的将来,人民行动党在现有的结构性优势下继续采用优势选举策略。这些来自国家机关和大众媒体之上的政治责任和有效影响, 这一选举制度是基于最高票者当选和多元选区选举原则,议会对宪法修正案的有效控制,和一个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霸权作为行动党的规则。尽管如此, 许多独裁政府的责任注定在一段时间内或在亚洲范围内外的巨大经济成就,必须给予人民行动党政府的一些原因来解释对民主压力长期积累和集约化的可能性的关注。更短的经济周期带来的威胁政治合法性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尤其发人深省。
在西方许多有影响的要素,包括在亚洲的经营跨国公司,全球科研院所,新保守派和社群主义者,在新加坡能够找到的这类社会和治理的各个方面都占有相当高的比重(罗丹与休伊森,1996)。然而,来自西方自由主义的批评者,通常会与当地反对派经常接触,这些人包括学者、记者、外交官员、人权团体甚至新加坡人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的海外,批判者往往将批评集中在温和官僚威权理论,这一理论也被称为“新加坡学校”。这是一个通过投票箱民主问责制的组合, 也是通过授予政府托管人民权利的权力和实现民族凝聚力的社会正义一个长期的方针政策;经估计这可以产生政治稳定,并且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Kausikan,1997年,第27页)。新加坡学校也一直被人民行动党政府贴上了代表西方颓废和虚伪的形象的“西洋化”标签,使用假人权的概念作为一种新殖民主义的工具。但最终,因为新加坡比其他方式更需要西方国家,人民行动党政府不能完全忽视人权的批评,特别是在国与国的水平上。
新加坡的自由民主化的前景也将取决于自下而上的力量如中产阶级、公民社会组织、学者和学生、大众媒体、艺术家以及对待国家历史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需求和不同的期望的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此外,自由民主化的这些驱动力正在受到全球发展的塑造。新加坡人经常出国工作,学习和假期。通过有线电视,他们可以不受限的看到全球新闻和娱乐。流行文化的导入,经过了一定程度的审查但几乎都是批发式的,来自美国、英国、香港、台湾、日本和韩国。随着1999年“今年智能城市”和世界上第四大主导信息经济和社会的国家(交通运输部,2001),新加坡将发现它几乎不可能被排除在全球影响之外,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可能认为这种影响对政治议程是有害的或无益的。
一般来说,尽管民主化的力量依然处于实验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协调的,经常没有落实到实践中去。例如,大多数中产阶级的新加坡人仍相对依赖人民行动党政府为他们的个人利益行政,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消费和生活方式问题,可能自己表现出了“专制”的个性(保罗,1992年,p25)。知识分子,警惕故意含糊其词的内部安全法,国家镇压仪器和普遍但概念狭隘的社会责任,他们变得自我监察,往往把注意力转移到更煽情的社会层面,因此不太理智(戈麦斯,2000)。首先,甚至年轻叛逆包含了高度竞争的教育系统,这一系统集中了有才华和表达能力的学生,这些学生在未来可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其次,变成了两年半的义务兵役(Tan,2001年,页。96 - 100年)。剩下的资源仍然是指向不关心政治的自愿社区服务团体。
开放、协商和参与
人民行动党将积极地影响某种公开,协商和参与社会政治现象的理由至少有三个。第一是在公众想象力力中知识驱动型的全球经济日益增长的霸主地位。根据广泛传播的言论,这样一种经济是一个了解技术阶梯的必要步骤,降低成本竞争力的解毒剂,抑制未来经济衰退影响的手段,一个普遍的前景是这种经济会激励员工不断升级自己以保持自己与经济的相关性。知识经济不仅需要通过技术能力,还需要足够开放,充满创意,创新,冒险和创业精神的创意社会来推动。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也可能是吸引有才华的外国人一个必要手段,这些有才华的外国人将大量推动新加坡知识经济的发展。而人民行动党政府可能会同意这些断言,他们不太可能公开采取一个开放的社会的定义作为一个放肆的,伦理和道德多元化,或者自由社会,这种自由社会由可能被现实取代的弱国政府的松散管理。然而, 即使没有强有力的民主政治,一个更加开放的环境,将意味着更少的家长式的政府能够并且愿意限制新闻,另类的想法和生活方式。
第二个推动力是日益增加的风险,政府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因为全球化民族国家的遭遇日益复杂的新旧问题。例如,外部依赖性的新加坡不能完全摆脱外部引起的经济衰退,1985年的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都证明了这点。就在1985年金融危机的不久前,反对党打破了人民行动党国会垄断,威胁要增加他们的议会席位。高性能经济委员会成立于1985年以应对经济衰退的影响,它提倡更多与私营部门沟通互联以充分利用前线资源来抢占先机和缓冲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的冲击力。增加与私营部门和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协商,人民行动党政府最近已确定为“人民部门”的基层组织,组成包括少数民族自助组织,自愿福利组织以及专业和民间组织, 这样可以保护人民行动党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和限制反对党在至少三个方面的前景。首先, 如果咨询一个快速成长的解决大量问题的资源池,人民行动党政府将执行得更好。毕竟,人民行动党不能假设在越来越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富裕的和全球性的新加坡人中有希望谋求公职以成为人民行动党成员的人。其次,增加咨询可以建立新的机制以拉拢潜在人员-将外部人员转入内部。第三,对协商的精心管理可以使人民行动党政府分散可能出现的故障的责任,同时仍允许其理所当然的成功。
第三推动增加福利的期望。据预测,到2030年,五分之一的人口将超过65岁(海峡时报周刊版,1999)。作为高技能新加坡人在全球竞争中谋求高收入, 低技能新加坡人只能与低工资工人竞争,这种竞争局面将会成为推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的楔子,加剧了现在俗称“数字鸿沟”。即使实际收入差距不会增加,在上下文中提到的对物质期望较高的年轻一代,在昂贵的房价和私人运输背景下,至少会感知到收入的差距。这些情况表明, 福利的压力可能在未来增加,这会迫使人民行动党政府采取不想屈服的福利主义路线。福利国家会把国家资源从生产和明显成功的经济发展体系中分离出来以支持一个机构的建立,政府认为这种机构会让不劳而获的人收益和降低努力工作激励机制。此外,人民行动党政府可能不完全具备处理福利问题的同时保持国家建设和经济增长的能力。防止政府超载和随之而来的合法性危机,人民行动党政府鼓励私人和“人民部门”包括宗教组织积极参与,在其监督下,进行福利、社区发展和国家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公民社会的社区发展理事会
允许公民社会成长但只能根据人民行动党政府自己的政党规则行事是有风险的政策。非政治性的民间组织,当在特定的(甚至是明确的)领域受制于政府时,可能会不愿意隐藏他们的批评或者是服从于政府。一旦民间社会发展起来,并假设新加坡人诚信,公开,协商和参与的预期收益可能会收获,但意想不到的政治后果仍是无法遏制,其中包括民间团体和反对党之间正在进行新的非正式联盟。对人民行动党政府来说, 对这种困境的回应是确定社区发展理事会作为另一个开放性,协商和参与的平台,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利用已经在政府控制下的基层来缓和公民社会的对抗势力,甚至成为基层部门的替代品。
目前有5个疾控中心管理着新加坡的中部、东北、西北、东南和西南地区,每个疾控中心由12到60名议员组成,这些议员主要由作为人民协会主席总理任命。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被任命为市长负责各地疾控中心。作为地方行政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任务是启动,规划和管理地区范围内的社区计划和项目,从中央部委接管越来越多的福利和社区发展的任务。国家为每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每年度每一居民1新元的拨款,通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努力和所有行政管理和运营成本全部资金募集将1新元的拨款提高到3新元或4新元。这些委员会提供的服务包括对贫困的新加坡人提供在医疗、住房和儿童养育津贴的资金援助;老年人医疗保健服务;技术培训机会和失业者的就业服务(《星期日泰晤士报》,2002年),家庭基础设施;志愿者宣传和部署, 以及通过艺术形式的社会宣传方案(社区发展委员会,2002)。
与中央政府机构不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根据成员所处的独特环境,利用当地知识和网络体系定制解决方案,以与人接触的方式来提供他们的服务,这样可以更有效地防止问题的产生和威胁社会凝聚力的现象出现。通过这种在一个屋檐下可以全方位提供可获得服务,面对复杂问题的家庭可以更容易找到全面的,多管齐下的解决方案。疾控中心可能成为普通新加坡人行使所有权并对决策结果责任的新的城市空间,在这种环境下,人们能更好地认识到自己在社区甚至国家中对他人的责任感,并学习重要的公民技能,比如如何有效参与公共辩论。曾有一些提议建议召开常规的区域会议,让传统的基层领袖和其他民间代表就市长和议员的工作进行提问和辩论,从而产生可能不那么正式的地方“议会”。议员致力于促进社会联系和提高社会凝聚力, 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试图通过与现有的基层、社区和公民组织增加合作来实现。但是,总理吴作栋一直小心翼翼地声称“没有打算让社区发展理事会取代自愿福利机构和基层组织或减少自愿福利机构和基层组织当前的角色和影响力”(吴,1997)。然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该与独立自主的公民社会组织合作成功吗,人民行动党政府将将在在一个大大扩展的社会中取得巨大的成就,这个社会是开放的,协商和参与性,同时在人民行动党政府庞大的网络控制中心下保持对这个社会政治限制。
改革基层的政治后果
传统的国家基层部门的民主问责制没有受到关注,因为其决策的权力是有限的。事实上,用人民行动党政府作政治工具,基层民主会适得其反。但是随着中央政府机构加大权力下放的力度,问责制的问题,责任和合法性将受到更多的关注。市长很有可能将继续从执政党的顶尖行列中任命。在更民主的当地政府中,市长作为掌握综合的政府职位的全职公职人员,市长需要超过在大学期间授权给他们的议员职位的更多的义务。在这样一个情景下,市长可以分别由各自的选区的选民选举产生或至少是有限的基层学院,社区和公民领袖。议员也可以通过选区范围或选举大学的选举产生。在这个更民主的当地政府,市长甚至不必是执政党的一员。
已提出的一个反对基层民主化的争论是基于国家的经验,这种国家经验是指民选产生的地方官员受制于既得利益,并愿意牺牲社会的更广泛需求(海峡时报,2000)。从人民行动党政府的立场看,这个反对基层部门民主化的言论是因为基层部门民主化不仅会减少其作为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政治工具的有效性,而且将设立一个可能被反对党利用的独立的政治空间。此外,由PAP代表自动管辖的区域开辟出了更多的机会让更多的城市和选区为换届选举投票活动服务,提高“地方选举战略”的有效性,特别是前面讨论过的“选票换升级战略”。此外, 有才华的非政治议员可能受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测试和训练,为PAP增选,成为潜在的国会议员选举候选人。
这些新的基层安排也同样作用于受传统基层部门影响下形成的传统的基层领导人。政府已经表明,一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150559],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以上是毕业论文外文翻译,课题毕业论文、任务书、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