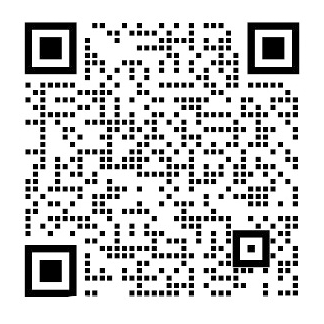附录三 外文文献原文
Cross-national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s i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thony F Jorm* and Siobhan M Ryan
Background There is a growing body of population survey data on national subjective well-being which allows comparisons across countries and across periods. Key issues in this work are as follows. Can response to questions on well-being be meaningfully compared across countries and periods? What social conditions are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well-being both between countries and across periods? Are there lessons for how global well-being might be improved? This review aims to give an overview of this area and its relevance to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Methods Systematic searches of the literature were carried out using eight academic databases between August 2012 and January 2013.
Result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volves multiple components, including cognitive evaluation of satisfaction with life and emotional state, and these are separable from mental ill health. Although there are difficulties in measur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omparable ways cross-culturally, there is sufficient evidence of validity to make comparisons meaningful.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nations increases with income per capita, but gains are smaller in higher income countries. Other national factors that affect well-being include income inequality, social welfare, individualism, democracy and freedom, social capital and physical health.
Conclusions Economic growth of lower-income nations will improve global subjective well-being. However, this needs to be sustainable or it will reduce the well-being of future generations. Higher-income nations need to focus on other determinants of well-being. Research on
cross-national well-being suggests a number of directions that may be profitably pursued in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Keywords Subjective well-being, happiness, life satisfaction, mental health, national differences, historical change
Introduction
There is now a very large literature on what has been termed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some of which is labelled under the rubric of happiness research or positive psychology. Given the size and diversity of this field, it is not possible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review in this paper. Rather the aim is to focus on a specific area, namely the determinants of national well-being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This is an area of research which is mainly pursued within psychology,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rather than within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Nevertheless, the issues investigated are of broad relevance to psychiatric epidemiologists. One of the aims of this review is to make national well-being research better known to an epidemiological readership and to consider what lessons might be learned for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Thus, we are interested in ecological studies that investigate SWB with the nation as the unit of analysis. Some studies examine both SWB and its predictors using national aggregates as data, whereas
others examine predictors of well-being at both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levels, and consider whether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re predictors of SWB after adjustment for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For example, does the income of a nation predict SWB over and above the income of the individuals who
make up the nation? Some predictors (e.g. democracy, political upheavals, inflation) can only exist at the national level, whereas others can exist at both levels (e.g. income, education). Some studies also investigate historical changes in SWB within nations, looking at whether changes in various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predict any changes in SWB. There are also differences in analytical approach between such studies. An important one is whether nation fixed effects are included in models.1 These capture unchanging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influences within nations, so that the correlations are basically between the change in a nationrsquo;s characteristic and change in the nationrsquo;s SWB, making most cross-sectional patterns disappear and reducing spurious correlations.
SWB is not a unidimensional construct. Factor analytical studies indicate that there is a cognitive component to SWB which involves an evaluation of satisfaction with life, and an affective component
which involves positive affect and the absence of negative affect.2 Whereas these components are correlated at both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levels, they are partly independent and may have somewhat different determinants. Positive affect, negative affect and life satisfaction are constructs associated with what has been called the hedonic view of SWB. An alternative to this is the eudaimonic view, which focuses on the extent to which a personrsquo;s life is in accordance with deeply-held values and the person is fully engaged.1 Measures derived from the hedonic and eudaimonic views are moderately correlated, indicating that the constructs are different but overlapping.
SWB is clearly related to, but different from, the constructs of mental ill health investigated by psychiatric epidemiologists. People who experience mental disorders or are suicidal score lower on measures of SWB.3 The strongest associations are with the negative affect component of SWB.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how strong correlations with negative affect. Depression is also related to lower positive affect, but to a lesser degree.4 These associations are to be expected, given that depressive disorders are defined as involving sad mood and loss of the ability to experience pleasure. It is also notable that depression screening questionnaires sometimes include items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measures of SWB. For example,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国家和历史的差异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Anthony F Jorm* and Siobhan M Ryan
背景:有越来越多的人口调查数据,以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进行比较,来显示国家的主观幸福感。这项工作有如下几个关键问题。对幸福感问题的回答可以在不同国家和时期进行有意义的比较吗?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有哪些社会条件和能获得更高的幸福有关?这些经验教训是否有能改善全球福祉?本文旨在概述该地区及其与精神病学流行病学的相关性。
方法;在2012年8月至2013年1月期间,使用了8个学术数据库,对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检索。
结果: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包括对生活和情绪状态的满意度的认知评价,这些因素与精神疾病无关。虽然在衡量主观幸福感方面有困难,但在跨文化的方面,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比较有意义的。国家的主观幸福感会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收入较高的国家的主观幸福感却减少了。其他影响幸福感的国家因素包括收入不平等、社会福利、个人主义、民主和自由、社会资本和身体健康等。
结论: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将改善全球的主观幸福感。然而,这需要可持续发展,否则后代的幸福感会减少。高收入国家需要关注其他与幸福有关的决定因素。有关跨国家幸福指数的研究表明,在精神病学流行病学中,可能会有大量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幸福、生活满意度、心理健康、民族差异、历史变化
介绍:
现在有一大批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文献,其中一些被称为幸福研究或积极心理学。鉴于此领域的规模和多样性,本文不可能提供全面的系统综述。相反,我们关注的是一个特定的领域,即从全球角度来看,国家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因素。这是一个研究领域,主要是在心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而不是在精神病学领域。然而,研究的问题与精神病学的流行病学家还是有广泛的相关性的。这项综述的目的之一,是使有关国家幸福感的研究更好地了解流行病学,并考虑从精神病学的流行病学方面学到了什么教训。
因此,我们对以国家为单位进行分析的生态研究很感兴趣。一些研究用国家总量作为数据,来研究总体幸福感量表和它的预测因子。还有一些人研究个人和国家层面的幸福指数,并考虑国家特征是否是已经对个体特征进行改编后的总体幸福感量表的一个预测因子。例如,一个国家的总体收入情况是否能预测那些超过个人平均收入的家庭的幸福感吗?一些预测者(如民主、政治动荡、通货膨胀)只能在国家层面上存在,而其他的预测者则可以同时存在于这两个层面(例如收入、教育)。一些调查还研究了国家内部总体幸福感量表的历史变化,研究各个国家特征的变化是否预示了其变化。这种研究的分析方法也有不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国家的固定影响是否包括在模型中。这些都是在对国家内部的文化和制度影响不改变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这些联系基本上是以国家特征和国家变化的变化来看的,使得大多数的横截面模式消失并且减少了虚假的相关性。
总体幸福感量表不是一个单维结构。有关因素分析的研究表明,SWB的认知成分包括对生活满意度的评价,以及情感成分,这包括积极影响和没有消极影响。尽管这些成分在个体和国家层面上都是相互关联的,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独立的,并且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决定因素。积极影响、消极影响和生活满意度这三点是与被称为“SWB”的快乐观相关的概念。另一种选择是快乐说视图,它关注的是一个人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与深度持有的价值观相一致,而且这个人是否是完全投入的。这与从享乐和快乐说的观点中得出的一项度量是适度相关的,这表明构造是不同的但是是有重叠的。
总体幸福感量表显然与精神疾病流行病学家所调查的精神疾病的结构有关。有精神障碍或有自杀倾向的人在总体幸福感的测量中得分较低。最大的关联是总体幸福感的负面影响部分。抑郁和焦虑与消极情绪有很强的相关性。抑郁也与较低的积极影响有关,但程度较低。这些关联是可以预料的,因为抑郁症被定义为涉及悲伤情绪和丧失体验能力快乐。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抑郁筛选调查表有时包括的项目与总体幸福感量表的度量密切相关。例如,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编制的抑郁症(ces - d)量表包括“我快乐”这一项。同样的,健康问卷也是一种常见精神疾病的筛选测试,包含一些能让你快乐、满意等其他一些积极的方面。
总体幸福感量表及其组件有很多度量标准。然而,大部分的国家数据来自于这个包括很多非常简短的措施的大型社会调查。主要的结论之一可以从表1看到,最常用的措施是衡量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单一项目。生活满意度项目衡量的是量表中的认知方面,并且与消极影响相比,积极影响的相关度更大,而幸福指数更具体地与积极影响相关。在研究民族差异的研究中,有7个幸福说概念并没有特别突出,尽管一些研究同时跨越了享乐和幸福的概念。尽管它们简短,但表1中的这些措施的可靠性在个人层面上是令人惊讶的好,例如,有超过0.70的人对在这一年内生活满意度很高。当聚集在国家层面上的时候,它要高得多。例如,在相同的调查系列中,这一年中的国家的平均生活满意度是0.93,而在不同的调查数据集中却变成了0.97。不同的总体幸福感量表指标的相关性也很高,在不同国家中,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水平的相关系数在0.85 - 0.87。这些国家统计的统计数据也与一些精神指标相关。在全国范围内,很幸福的比例被发现与自杀率的相关指数是0.37,而国家总体幸福感量表上的这两个指标分别为0.46和0.66,这两个指标是从国家层面上在贝克抑郁量表上测量的。同样,国家主观幸福感的综合指标与精神疾病的综合指标的相关系数为0.60。
比较这些在简单问题在不同国家的反应,这个问题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这些措施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有效的比较,像语言和文化群体。在跨文化条件的相比之下,有不同的证据都可以表明总体幸福感量表的措施倾向于给予具有可比性的国家排名;例如,体验瞬间的抽样情绪的方法 ,相比更常用的问卷调查,微笑和记忆的频率对于好的和坏的事件的影响已经很普遍了。此外,双语者对每个人的评价都是相似的,拥有多种语言的国家为每种语言提供了类似的评分组。积极的和消极的因素被发现在不同的文化中也是可比较的。在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相信个人主义者文化的人对幸福感量表的评价有些不同于跟随集体主义文化的人们,前者认为情感更重要,后者认为社会规范重要。还有一些关于差异的证据在国家间使用范围很广,也就是当评估可比性的评级被发现时。在一个国家内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幸福感量表似乎不太容易受到这些问题的影响,因为在这些项目中的改变在几十年内都是很小的。然而,暴露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更大的改变在于,教育或电视可能会微妙的变化词语的含义。像“同性恋”这个词,在这一代人的意义上已经发生了变化,显示了快速的语义变化。
方法:
根据相关研究,在八个学术数据库(学术搜索)中进行了完整的搜索,(谷歌学者,Medline,PsycARTICLES,心理信息,心理和行为科学,斯特拉斯和SocINDEX)在2012年8月至2013年1月,利用不同的数据库,使用与幸福感量表相关的搜索词搜索数据库(“幸福”、“幸福”或“生活满意度”“积极影响”或“幸福”,以及与之相关的术语国家差异(国家差异)“国家”或“跨越国家”或历史变化(“历史变化”或“历史差异”或“跨越”历史”或“历史”)。本文的物质性的参考清单,在最初是利用手工来搜索其他相关来源。这项研究包括把SWB作为结果(而不是预测者)的度量,并在国家层面上检查数据,跨越国家或国家的不同时间。研究被排除在外,如果他们的评论是这样的,没有任何报告或新的分析,用的是精神疾病的措施,而不是SWB或专注于a的SWB特定年龄组(例如:学生或老年人)。不限制出版日期,使用这些标准,我们的初始搜索定位为367个出版物,在申请后减少到78个包含和排除标准在内的出版物。
结果
关键数据和复制问题,有许多新的研究报告分析国家主观幸福感数据,但这个数字是骗人的。大多数研究是基于一个相对较小的数字的数据集,主要的总结可以从表2看出来。这些数据集都提供了一个或多个维度来调查国民幸福感。这些数据集的研究经常用国家特性数据配对来自其他数据集。因为这些其他数据集可能涵盖的范围不是同一个国家,对于分析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即使在出版时使用相同的主观幸福感数据。此外,一些数据涉及重复调查,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的时间点可能会对类似的问题进行不同的分析。由于这些原因,很难把出版物作为独立的或说它是一个已经被复制的发现。
这一文献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国民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因子具有高度相关性。
虽然许多预测者显示出强烈的联想,但单独检查时,这些倾向在多变量分析中会减少或消失。对于这个原因,预测可能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根据其他因素进行调整。这个文献中发现的主要预测因子,将按国民生产总值衡量国民收入人均或其他指标。因此,在这篇文章中的其他所有的预测因子考虑到研究结果,已经最低限度地调整为国家收入。
主观幸福感的替代措施。如前所述,国家的主观幸福感是最常见的生活满意度,幸福或情感汇总统计测量,然而,有许多选择已经提出了一些不被审查的措施,他们在文献中收集到的任何细节,都给予了有限的关注。这些包括繁荣(
结合了快乐和幸福说方面的幸福感),主观不平等,不平等调整幸福,这些措施可能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国家主观幸福感规范。在国家调查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是,倾向于认为自己快乐或满意生活。例如,当生活满意度定义为从0到100时,大多数在高度发达国家的人的得分在40到100之间,平均得分在75分左右,甚至最低的国家的得分也超过了50。这一发现被解释为暗示主观幸福感可能要服从于家庭静态机制。
国民收入,预测检查最经常的跨国研究一直是研究国家收入,如实际的人均收入。一致的联想发现在不同的数据集中的全国主观幸福感,并且在其他方面调整了其余预测因子。虽然大部分证据是从国家层面研究的,国民收入个人调整后,还能进行多层次的预测吗。从图中可以知道,还是有较强的关联的,在较贫穷的国家,相较于平均国民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也比较平稳。如果一个对数转型适用于收入,联系会变成线性的(如图1所示)。该国国民收入可能会更高,也就会有更强的生活满意度,相比于影响措施。
也有大量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使用时间序列数据。一个由理查德bull;伊斯特林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横截面数据,根据来自美国的时间序列数据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主观幸福感没有增加,尽管人均实际收入稳步增长。这幸福收入悖论,或伊斯特林悖论,继续成为辩论的主要来源。如果这是真的,这悖论意味着经济增长不应该政策的主要目的。支持后续研究伊斯特林的观察,主观幸福感也没有尽管经济增长在美国有所改善,但改进已观察到其他高收入国家,包括在欧洲和日本。然而,也有证据表明,经济快速增长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不快乐会增长),如果它导致更大的不平等,超越成就的愿望。这种现象已被观察到,例如,在中国从1990到本世纪初。更复杂时间序列分析发现证据表明经济增长与主观幸福感相关。他和他的同事们还进行了更多的来自几个国家的数据的最近时间序列分析。他们认为收入确实会影响主观幸福感在短期内,但长期来看(10年以上)没有收获。另一种观点是,提高收入确实有一个主要短期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有一个较小的长期效应,使之有持久的收益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好处还在继续,经过辩论,但似乎有证据证明,收入增加的好处是富裕的国家比更贫穷的国家已经提出了许多解释收益递减的原因。这些包括受相对收入的影响更大,比绝对收入高,富裕国家的人适应增加他们的收入,其他领域的变化(更长的工作时间)抵消了收益收入增加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允许我们满足基本的需求,一旦满足了这些需求,就不容易获得。一般认为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只会增加在高收入国家,如果允许的话人们追求有意义的活动有意义的目标,比如改善亲密关系或者工作生活的质量。有也有人建议国家可以通过改变参照组,来比较他们自己(例如他们的祖先。)更糟糕的是,人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寻找幸福的价值,在非金钱领域(例如家庭生活)哪一个更少受适应和社会和收入的影响。最后,这可能是由国民收入之间的联系形式的,而不是由是有意义的决定的,因为使用序数尺度来测量幸福感。它可以认为,在有顺序的规模内,任何单调转换都是可以接受的。
收入不平等,有一些分析收入不平等像在人均收入之上的,是否会影响到主观幸福感。因为高收入国家的不平等往往更少,这是必要的因为这个收入是可以调整的。例如,在一个以54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国家级研究上,人均GDP和基尼系数存在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84,使得它很难在回归分析中分离这些谓词。这一研究,在调整了收入后,发现不平等并没有额外的预测能力。相比之下,最近的一个在51个国家中进行的国家级分析发现了,在收入调整后,主观幸福感量表中对不平等的影响还是在的。但在这个分析中,有一个不同的指标,收入不平等被用在只有0.45的较低的相关性人均GDP上。多层次的分析的作用主要是支持收入不平等。利用欧洲数据的两个多层次分析发现,不平等与幸福感较低有关,在对个人和国家进行收入进行调整之后。相比之下,对来自41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多层次的分析,发现了不平等的预测了较高的主观幸福感,在对个人和个人的收入进行调整后。然而,这一发现是由于包括拉丁美洲和后苏联国家,前者具有高度的不平等,但是较高的主观幸福感,以及后者具有低水平的不平等和低水平的幸福感。但在过去25年间对8个高收入国家的时间性的数据的变化中可以发现,幸福感的变化导致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这与幸福感的增加相关。
社会福利和累进税制,社会福利和累进税制的程度是其他与收入不平等密切相关的变量。在一个对40个国家进行分析的国家级研究中发现,社会保障支出与主观幸福感没有联系。相反,在一个对12个欧洲国家进行时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484714],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