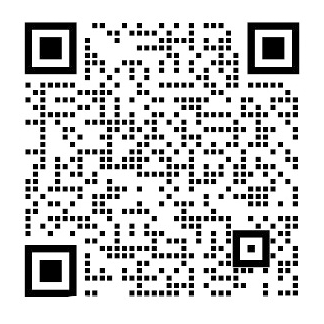Philippe C. Duchastel. Research on Illustrations in Text: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amp; Technology, 1980, 28 (4):283-287.
文本插图研究:论点和看法
摘要:许多研究都未能指明插图在文本和教材中的显著效果。作者指出,如果研究是在浅层次进行的,那么就不难相信插图在学习中确实没有帮助作用。但是作者认为目前来讲已经有充足的研究能证明插图的价值,只是这些研究只能支持简单的论断,研究者必须继续深入探索,用新的观点去研究插图能帮助学习的原因。
关键词:插图;学习 ;教学
插图在教科书和其他教学材料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并且对于教学设计者来说,对插图的研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尽管长久以来传统教科书的设计都是基于创造性直觉和隐性知识的,但大量对插图的实验研究得出的结果却与对这种直观观点的预期相去甚远。如此多的研究都没能显示出插图的显著效果,如果研究是在浅层次上进行的,那么让人不得不相信插图在学习中确实是没有帮助作用的。
艺术的现状确实是混乱的,并且当涉及到教科书插图的实用艺术时,教学设计者除了质疑研究成果并继续依靠创造性本能外并没有其他选择。这篇文章的主题之一是,目前研究仍然给了我们一个不恰当的观点,即过分消极且违反常理。从失败中得不到什么,从成功中也得不到更多。以前的许多研究都只是试图证明插图可以对学习产生影响,而且还经常失败。正如Denburg(1976-77)所说,研究插图是否能提高学习能力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为什么以及如何做到这一点。研究文本中插图的观点已经开始出现,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引起人们对这一观点的注意。
由于对文本中插图的研究已经有了许多相应的报告,我考虑更多的是观点问题而不是该领域的详细发现。我的观点部分基于对研究报告文献的回顾(Duchastel,1980),之前的报告也是结构化的。Samuels(1970)的报告是比较著名的,尤其是其中关于在阅读教学中使用插图的结论。Carroll(1971)在从言语学习的报告中更简明地对插图进行了讨论。Holliday在一篇杰出的报告中对研究进行了实践研究,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一个主题,同时也引出了MacDonald Ross的两篇综述,一篇是对定量信息描述研究的全面回顾(1977),另一篇是对文本图形的回顾(1978)。Fleming(1979)最近也发表了一篇有意义的报告。
Levin和Lesgold(1978)对一个领域的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他们研究的是图片在口语叙事(听故事)中的作用。然而,当时的研究情况与从文本中学习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尽管报告的标题有些误导性)。因而口语故事中的插图研究起码还需要扩大到阅读情境中去。
- 插图研究中的问题
插图不是教学文本的单一组成部分。术语“插图”(或图片)是一个通用词语,它涵盖了诸如照片、示意图、图表和地图等各种元素。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询问图片是否有助于学习就与询问音乐是否有助于跳舞一样。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音乐的种类,同样的,图片是否有助于学习就取决于图片的类型和质量。文本图片可以选择得很好,也可以选择得很差;图表可以是清晰的、切题的,也可以是模糊的、难以解释的(参见MacDonald Ross,1977,了解这些方面的一些详细观点)。
插图存在于文本中也一定是有明确目的的。仅仅把各种各样的、看似相关的图片放在这里或那里,然后琢磨这些图片是否有助于学习就是在自找麻烦。因此,任何对插图的研究都存在一个难题,那就是恰当性问题,不幸的是很难判断这一点——也许这个问题在插图上比教学的其他地方更明显,因为插图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插图相关研究结果中的许多模棱两可之处都与适当性问题有关。
毫无疑问,含插图散文材料的类型和读者的水平是与研究相关的一个困难之处。一本有插图的儿童故事与一本有插图的大学教科书大不相同。因此,人们越是考虑插图的范围,无论是在多样性还是背景上,就越不会因为这些年来研究结果缺乏一致性而感到惊讶。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缓解我们个人本能的倾向,并从适合的角度看待研究得出的结论。事实上,研究结论只是整个议题的一部分,并且受到有关插图问题的范围的限制。
图片的效果必须从三个单独的领域考虑:理解、回忆和动机。理解和回忆往往很难分开,特别是当根据早期教育中使用的课文来衡量学习时。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是否应从这三个领域加以区分是有些令人犹豫的。然而,从绘画的角度来看,这种区别是有意义的,因为插图的解释功能可能与它们的保留记忆功能非常不同(Duchastel,1978)。这一区别已经在许多研究中得到了区分,但不幸的是,之前通常不是在很强的操作条件下进行区分的。
关于理解效果的结论应该从那些插图有一定效果的研究中得出,因为剩余部分的研究缺乏效果的原因都是遇到了特殊困难,因而无法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事实上,在适当的情况下插图毫无疑问可以帮助学习,在书籍设计中应该鼓励使用插图。这是高质量图形文本优良且长久的设计传统。
尽管有一些研究表明插图会阻碍理解,但仍有大量的研究并没有显示出这一点(Duchastel,1980年)。很难判断这些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对所讨论的假设进行了良好试验。插图对理解力的影响究竟是大还是小?从科学课本中得到的经验让人相信后者是可能的。其实文本内容的类型是必须加以考虑的,有些材料不需要插图来帮助理解,而同时其他材料则需要。考虑到这一点,人们真的应该质疑全球普遍衰落的问题是否值得提出。
毫无疑问,回忆有时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的,因为更易理解的文本将被更好地保留在记忆中(参见Doolingamp;Lachman的有趣的《共感效应研究》,1971年)。回忆效应在教科书插图领域是一个受认可的关注领域,因为相较于文字,人们更容易通过图片获得深刻的记忆(Paivio,1975)。
尽管回忆被认为常常会与理解力混淆,但大量研究表明插图可以帮助增强回忆(Duchastel,1980)。然而,大多数研究只研究了即时回忆效应;很少有研究去验证假设的有力性,而这一假设认为插图文本能促进长时记忆的保留。
传统上,书中有插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使书更具吸引力并且更能吸引读者,同时从出版商的角度来看,有插图的书籍更具市场价值。事实上,有人认为最基础的读者也应该看有插图的书,他们提出来这点的原因之一就是插图能增强阅读兴趣。尽管出版公司进行的很多市场调研都无疑是支持之前说的这种直觉的,但我不知道有哪些教育研究直接研究了这个问题。因此出于探究动机的目的,插图的价值必须在直观的基础上被接受——这样做是完全合理的。
综上所述,研究似乎对文本插图的实践领域影响不大。至少,这是大多数研究得出的结果。在试图确认文本插图价值的过程中,看起来是失败多于成功的。尽管如此,插图无疑会被理解得比文学中描绘的更美好。插图可以帮助学习,就理解和回忆而言,这点已经在许多研究中得到证明——这就是他们在教科书设计中保有坚定信念所需要的价值所在。
研究表明,插图的不当使用可能存在一定的危险,如在“视觉词汇教学”的某些特定安排中。人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确定哪些插图是有害的,哪些是有益的,以及是否有必要对某些影响进行权衡(例如,以较慢的学习进度为代价来增加兴趣)。这个问题无疑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研究在对抗极端想法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例如越实事求是的图片就是越好的图片这样的极端想法。德怀尔的研究(1972)在很大程度上批判了这种想法。
另一方面,Dwyer对同一基础材料和插图的大量研究也证实了该方面的变化无常,也就是说,它对条件的微小变化有一定的敏感性。Dwyer研究发现,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变量(如图片大小和学生所处年级)与插图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再加上引言中提到的更为根本的困难,这一领域反复无常的性质会导致人们无法对研究的多次失败进行深入思考,以确定文本中插图的价值。
- 研究框架
为了建立指导未来研究的框架,学者们已经尝试对插图领域进行了分析。Dwyer对现实主义程度的思考绝对是这方面的典范。有学者在建立插图分类法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大胆的尝试(Fleming,1967年;Twyman,1979年),尽管后续缺乏了热情,也许是因为将分类法建立在图片的物理属性上而不是沟通意图上存在着固有困难(Duchastel,1978;Knowleton,1966;Novitz,1977)。
同样地,同模式标本已经被开发出来(Neurath,1974年)作为一套指导图形设计师描述定量信息的原则(参见MacDonald-Ross,1977年)。更笼统地说,史密斯(1960)为教科书插图制定了许多创造性原则,尽管这些原则不适合任何整体理论框架。这两套原则对需要使用文本插图的教育者都是有用的,但这些原则是否能带来强有力的研究框架仍值得怀疑。他们做的是引导我们走向一个用于说明的功能框架,而不是基于物理属性的初始框架。这一转变对未来的插图研究是重要的,它朝向了一个观点,即一幅图片的外观是次要问题,主要问题是需要集中一幅图片在其特定语境下的作用。我坚信,在插图研究中功能性方法将会取代形态性方法。
以往许多插图相关研究显示了对功能理论的直观认识,但还是很少有人尝试将其系统化。Knowlton(1966)以将图片分类为逼真的、相似的和合逻辑的方式提供了线索。逼真的图片被用来直接表示某种东西(例如,一只渡渡鸟的外形),而相似的图片则是一个明喻(例如,在一本生物学书中,两个伐木工人移动一棵伐倒的树,树代表一根骨头,而伐木工人则是肌肉——由knowlton给出的例子)。至于合逻辑图像,它们把要表示的内容进行了图解(地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图片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展示”以达到它们的效果,并且它们这样做的方式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被有效考虑到。
最近一种更为全球性的功能理论被提出(Duchastel,1978年),其中插图被认为具有引起注意、解释说明和保留情境的作用。换句话说,插图可以包含在文本中,以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动力,帮助解释散文中的观点,或增进对散文的长期回忆。这些功能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插图文本设计的实际过程加入了对强调和协调权衡的考虑。
Levin(1979)独立提出了第二种图片研究的功能理论。他的方法确定了八种插图在文本中可能具有的功能。Duchastel和Levin两人的方法都具有很强的功能性,可能代表了插图研究将来的一个有影响力的方向。
综上所述,尽管文本中插图的价值在一些研究中未能证实,但它们已经被更多的研究所证实,并且在证实的过程中坚持了长期的传统所确立的信念,而这正是图形设计的实践部分。研究人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使用新的观点来发现插图有助于学习的原因。只有这样,研究才能为未来的实践提供信息。Janan Faraj Falah. The Influence of the Illustrations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Hebrew Written Text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in the Arab Sector in Israel[J]. Creative Education,2018,09(01).
插图对以色列阿拉伯地区小学希伯来文字理解的影响
摘要:本文探讨了希伯来教科书中插图对学生理解文本的影响,以及学生在理解书面文本的过程中使用这些插图中的细节的程度。此外,学者还对插图在课堂上对学生想象力的影响进行了讨论。阿拉伯学生在一二年级学习了母语后,于三年级开始学习希伯来语。这一过程需要很大的努力,因为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之间的差距很大。当学生开始学习希伯来语并以之为第二语言时,大多数教师使用各种各样的插图来进行教学。使用图片来描述单词是第一个阶段,然后使用插图来呈现文本的主题是下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插图帮助不能很好学习新词的学生更好地理解教科书中的内容,提高其希伯来语的学习效率。本研究通过希伯来语课堂观察和对阿克里州Terra Santa School学校三、四年级学生的访谈,探讨插图与教科书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插图;希伯来语;第二语言;教学策略;以色列阿拉伯地区;小学
- 引言
一般来说,教科书中的插图,特别是儿童文学中的插图,都是一种直观的反映,因为绘图者会为一定的概念重点绘制插图(Gonen,1997)。儿童教育学的、社会的或国家相关的故事可能会在其插图中蕴含双重信息,包括隐藏的或开放的,以传达信息(Faraj Falah,2013年)。
插图使书更具创造性和艺术性(Nodelman,1988),它是视觉交流的语言,也是现代文化的主要沟通形式之一(Shavid,1996)。儿童书籍中的插图具有一定的作用,一种是展示性的——展示出文本中的细节和情境,另一种是知识性的——准确解释儿童无法想象的部分。
历史上,有插图的印刷书籍是过去手写稿和媒体的直接发展。书写是绘画逐渐演变而来的,在墙上用象形文字装饰手稿时,书写就转变成了视觉图像,并且是由人和动物的视觉方向决定的。在后期,宗教副标题也被写在教堂的墙上(Gonen,1997年)。儿童读物中的插图是17世纪出现的一种相对较新的历史现象,用于缓解儿童在漫长乏味的学校生活中的学习困难。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改革主要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加速进行,涉及到了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更广泛的美学和教学方面(Gonen,2013年)。
如前所述,18世纪的英国公民已经更加意识到教育对于未来“爬上社会阶层”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开始添加专门为儿童设计的、独特的插图(特别的装饰,如带有强烈的明亮色彩的书的封面),以吸引孩子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Philippe C. Duchastel. Research on Illustrations in Text: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 amp; Technology, 1980, 28 (4):283-287.
文本插图研究:论点和看法
摘要:许多研究都未能指明插图在文本和教材中的显著效果。作者指出,如果研究是在浅层次进行的,那么就不难相信插图在学习中确实没有帮助作用。但是作者认为目前来讲已经有充足的研究能证明插图的价值,只是这些研究只能支持简单的论断,研究者必须继续深入探索,用新的观点去研究插图能帮助学习的原因。
关键词:插图;学习 ;教学
插图在教科书和其他教学材料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并且对于教学设计者来说,对插图的研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尽管长久以来传统教科书的设计都是基于创造性直觉和隐性知识的,但大量对插图的实验研究得出的结果却与对这种直观观点的预期相去甚远。如此多的研究都没能显示出插图的显著效果,如果研究是在浅层次上进行的,那么让人不得不相信插图在学习中确实是没有帮助作用的。
艺术的现状确实是混乱的,并且当涉及到教科书插图的实用艺术时,教学设计者除了质疑研究成果并继续依靠创造性本能外并没有其他选择。这篇文章的主题之一是,目前研究仍然给了我们一个不恰当的观点,即过分消极且违反常理。从失败中得不到什么,从成功中也得不到更多。以前的许多研究都只是试图证明插图可以对学习产生影响,而且还经常失败。正如Denburg(1976-77)所说,研究插图是否能提高学习能力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为什么以及如何做到这一点。研究文本中插图的观点已经开始出现,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引起人们对这一观点的注意。
由于对文本中插图的研究已经有了许多相应的报告,我考虑更多的是观点问题而不是该领域的详细发现。我的观点部分基于对研究报告文献的回顾(Duchastel,1980),之前的报告也是结构化的。Samuels(1970)的报告是比较著名的,尤其是其中关于在阅读教学中使用插图的结论。Carroll(1971)在从言语学习的报告中更简明地对插图进行了讨论。Holliday在一篇杰出的报告中对研究进行了实践研究,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一个主题,同时也引出了MacDonald Ross的两篇综述,一篇是对定量信息描述研究的全面回顾(1977),另一篇是对文本图形的回顾(1978)。Fleming(1979)最近也发表了一篇有意义的报告。
Levin和Lesgold(1978)对一个领域的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他们研究的是图片在口语叙事(听故事)中的作用。然而,当时的研究情况与从文本中学习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尽管报告的标题有些误导性)。因而口语故事中的插图研究起码还需要扩大到阅读情境中去。
- 插图研究中的问题
插图不是教学文本的单一组成部分。术语“插图”(或图片)是一个通用词语,它涵盖了诸如照片、示意图、图表和地图等各种元素。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询问图片是否有助于学习就与询问音乐是否有助于跳舞一样。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音乐的种类,同样的,图片是否有助于学习就取决于图片的类型和质量。文本图片可以选择得很好,也可以选择得很差;图表可以是清晰的、切题的,也可以是模糊的、难以解释的(参见MacDonald Ross,1977,了解这些方面的一些详细观点)。
插图存在于文本中也一定是有明确目的的。仅仅把各种各样的、看似相关的图片放在这里或那里,然后琢磨这些图片是否有助于学习就是在自找麻烦。因此,任何对插图的研究都存在一个难题,那就是恰当性问题,不幸的是很难判断这一点——也许这个问题在插图上比教学的其他地方更明显,因为插图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插图相关研究结果中的许多模棱两可之处都与适当性问题有关。
毫无疑问,含插图散文材料的类型和读者的水平是与研究相关的一个困难之处。一本有插图的儿童故事与一本有插图的大学教科书大不相同。因此,人们越是考虑插图的范围,无论是在多样性还是背景上,就越不会因为这些年来研究结果缺乏一致性而感到惊讶。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缓解我们个人本能的倾向,并从适合的角度看待研究得出的结论。事实上,研究结论只是整个议题的一部分,并且受到有关插图问题的范围的限制。
图片的效果必须从三个单独的领域考虑:理解、回忆和动机。理解和回忆往往很难分开,特别是当根据早期教育中使用的课文来衡量学习时。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是否应从这三个领域加以区分是有些令人犹豫的。然而,从绘画的角度来看,这种区别是有意义的,因为插图的解释功能可能与它们的保留记忆功能非常不同(Duchastel,1978)。这一区别已经在许多研究中得到了区分,但不幸的是,之前通常不是在很强的操作条件下进行区分的。
关于理解效果的结论应该从那些插图有一定效果的研究中得出,因为剩余部分的研究缺乏效果的原因都是遇到了特殊困难,因而无法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事实上,在适当的情况下插图毫无疑问可以帮助学习,在书籍设计中应该鼓励使用插图。这是高质量图形文本优良且长久的设计传统。
尽管有一些研究表明插图会阻碍理解,但仍有大量的研究并没有显示出这一点(Duchastel,1980年)。很难判断这些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对所讨论的假设进行了良好试验。插图对理解力的影响究竟是大还是小?从科学课本中得到的经验让人相信后者是可能的。其实文本内容的类型是必须加以考虑的,有些材料不需要插图来帮助理解,而同时其他材料则需要。考虑到这一点,人们真的应该质疑全球普遍衰落的问题是否值得提出。
毫无疑问,回忆有时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的,因为更易理解的文本将被更好地保留在记忆中(参见Doolingamp;Lachman的有趣的《共感效应研究》,1971年)。回忆效应在教科书插图领域是一个受认可的关注领域,因为相较于文字,人们更容易通过图片获得深刻的记忆(Paivio,1975)。
尽管回忆被认为常常会与理解力混淆,但大量研究表明插图可以帮助增强回忆(Duchastel,1980)。然而,大多数研究只研究了即时回忆效应;很少有研究去验证假设的有力性,而这一假设认为插图文本能促进长时记忆的保留。
传统上,书中有插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使书更具吸引力并且更能吸引读者,同时从出版商的角度来看,有插图的书籍更具市场价值。事实上,有人认为最基础的读者也应该看有插图的书,他们提出来这点的原因之一就是插图能增强阅读兴趣。尽管出版公司进行的很多市场调研都无疑是支持之前说的这种直觉的,但我不知道有哪些教育研究直接研究了这个问题。因此出于探究动机的目的,插图的价值必须在直观的基础上被接受——这样做是完全合理的。
综上所述,研究似乎对文本插图的实践领域影响不大。至少,这是大多数研究得出的结果。在试图确认文本插图价值的过程中,看起来是失败多于成功的。尽管如此,插图无疑会被理解得比文学中描绘的更美好。插图可以帮助学习,就理解和回忆而言,这点已经在许多研究中得到证明——这就是他们在教科书设计中保有坚定信念所需要的价值所在。
研究表明,插图的不当使用可能存在一定的危险,如在“视觉词汇教学”的某些特定安排中。人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确定哪些插图是有害的,哪些是有益的,以及是否有必要对某些影响进行权衡(例如,以较慢的学习进度为代价来增加兴趣)。这个问题无疑将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研究在对抗极端想法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例如越实事求是的图片就是越好的图片这样的极端想法。德怀尔的研究(1972)在很大程度上批判了这种想法。
另一方面,Dwyer对同一基础材料和插图的大量研究也证实了该方面的变化无常,也就是说,它对条件的微小变化有一定的敏感性。Dwyer研究发现,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变量(如图片大小和学生所处年级)与插图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再加上引言中提到的更为根本的困难,这一领域反复无常的性质会导致人们无法对研究的多次失败进行深入思考,以确定文本中插图的价值。
- 研究框架
为了建立指导未来研究的框架,学者们已经尝试对插图领域进行了分析。Dwyer对现实主义程度的思考绝对是这方面的典范。有学者在建立插图分类法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大胆的尝试(Fleming,1967年;Twyman,1979年),尽管后续缺乏了热情,也许是因为将分类法建立在图片的物理属性上而不是沟通意图上存在着固有困难(Duchastel,1978;Knowleton,1966;Novitz,1977)。
同样地,同模式标本已经被开发出来(Neurath,1974年)作为一套指导图形设计师描述定量信息的原则(参见MacDonald-Ross,1977年)。更笼统地说,史密斯(1960)为教科书插图制定了许多创造性原则,尽管这些原则不适合任何整体理论框架。这两套原则对需要使用文本插图的教育者都是有用的,但这些原则是否能带来强有力的研究框架仍值得怀疑。他们做的是引导我们走向一个用于说明的功能框架,而不是基于物理属性的初始框架。这一转变对未来的插图研究是重要的,它朝向了一个观点,即一幅图片的外观是次要问题,主要问题是需要集中一幅图片在其特定语境下的作用。我坚信,在插图研究中功能性方法将会取代形态性方法。
以往许多插图相关研究显示了对功能理论的直观认识,但还是很少有人尝试将其系统化。Knowlton(1966)以将图片分类为逼真的、相似的和合逻辑的方式提供了线索。逼真的图片被用来直接表示某种东西(例如,一只渡渡鸟的外形),而相似的图片则是一个明喻(例如,在一本生物学书中,两个伐木工人移动一棵伐倒的树,树代表一根骨头,而伐木工人则是肌肉——由knowlton给出的例子)。至于合逻辑图像,它们把要表示的内容进行了图解(地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图片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展示”以达到它们的效果,并且它们这样做的方式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被有效考虑到。
最近一种更为全球性的功能理论被提出(Duchastel,1978年),其中插图被认为具有引起注意、解释说明和保留情境的作用。换句话说,插图可以包含在文本中,以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动力,帮助解释散文中的观点,或增进对散文的长期回忆。这些功能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插图文本设计的实际过程加入了对强调和协调权衡的考虑。
Levin(1979)独立提出了第二种图片研究的功能理论。他的方法确定了八种插图在文本中可能具有的功能。Duchastel和Levin两人的方法都具有很强的功能性,可能代表了插图研究将来的一个有影响力的方向。
综上所述,尽管文本中插图的价值在一些研究中未能证实,但它们已经被更多的研究所证实,并且在证实的过程中坚持了长期的传统所确立的信念,而这正是图形设计的实践部分。研究人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使用新的观点来发现插图有助于学习的原因。只有这样,研究才能为未来的实践提供信息。Janan Faraj Falah. The Influence of the Illustrations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Hebrew Written Text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in the Arab Sector in Israel[J]. Creative Education,2018,09(01).
插图对以色列阿拉伯地区小学希伯来文字理解的影响
摘要:本文探讨了希伯来教科书中插图对学生理解文本的影响,以及学生在理解书面文本的过程中使用这些插图中的细节的程度。此外,学者还对插图在课堂上对学生想象力的影响进行了讨论。阿拉伯学生在一二年级学习了母语后,于三年级开始学习希伯来语。这一过程需要很大的努力,因为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之间的差距很大。当学生开始学习希伯来语并以之为第二语言时,大多数教师使用各种各样的插图来进行教学。使用图片来描述单词是第一个阶段,然后使用插图来呈现文本的主题是下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插图帮助不能很好学习新词的学生更好地理解教科书中的内容,提高其希伯来语的学习效率。本研究通过希伯来语课堂观察和对阿克里州Terra Santa School学校三、四年级学生的访谈,探讨插图与教科书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插图;希伯来语;第二语言;教学策略;以色列阿拉伯地区;小学
- 引言
一般来说,教科书中的插图,特别是儿童文学中的插图,都是一种直观的反映,因为绘图者会为一定的概念重点绘制插图(Gonen,1997)。儿童教育学的、社会的或国家相关的故事可能会在其插图中蕴含双重信息,包括隐藏的或开放的,以传达信息(Faraj Falah,2013年)。
插图使书更具创造性和艺术性(Nodelman,1988),它是视觉交流的语言,也是现代文化的主要沟通形式之一(Shavid,1996)。儿童书籍中的插图具有一定的作用,一种是展示性的——展示出文本中的细节和情境,另一种是知识性的——准确解释儿童无法想象的部分。
历史上,有插图的印刷书籍是过去手写稿和媒体的直接发展。书写是绘画逐渐演变而来的,在墙上用象形文字装饰手稿时,书写就转变成了视觉图像,并且是由人和动物的视觉方向决定的。在后期,宗教副标题也被写在教堂的墙上(Gonen,1997年)。儿童读物中的插图是17世纪出现的一种相对较新的历史现象,用于缓解儿童在漫长乏味的学校生活中的学习困难。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改革主要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加速进行,涉及到了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更广泛的美学和教学方面(Gonen,2013年)。
如前所述,18世纪的英国公民已经更加意识到教育对于未来“爬上社会阶层”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开始添加专门为儿童设计的、独特的插图(特别的装饰,如带有强烈的明亮色彩的书的封面),以吸引孩子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英语原文共 16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72348],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以上是毕业论文外文翻译,课题毕业论文、任务书、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