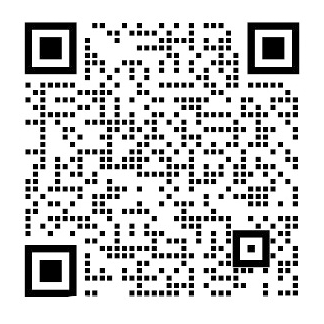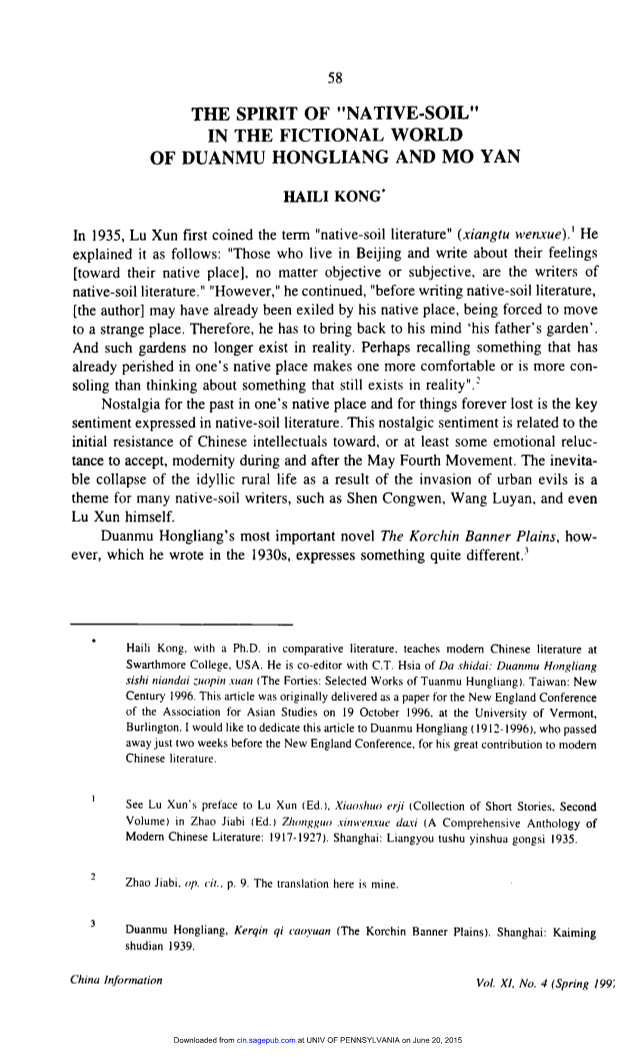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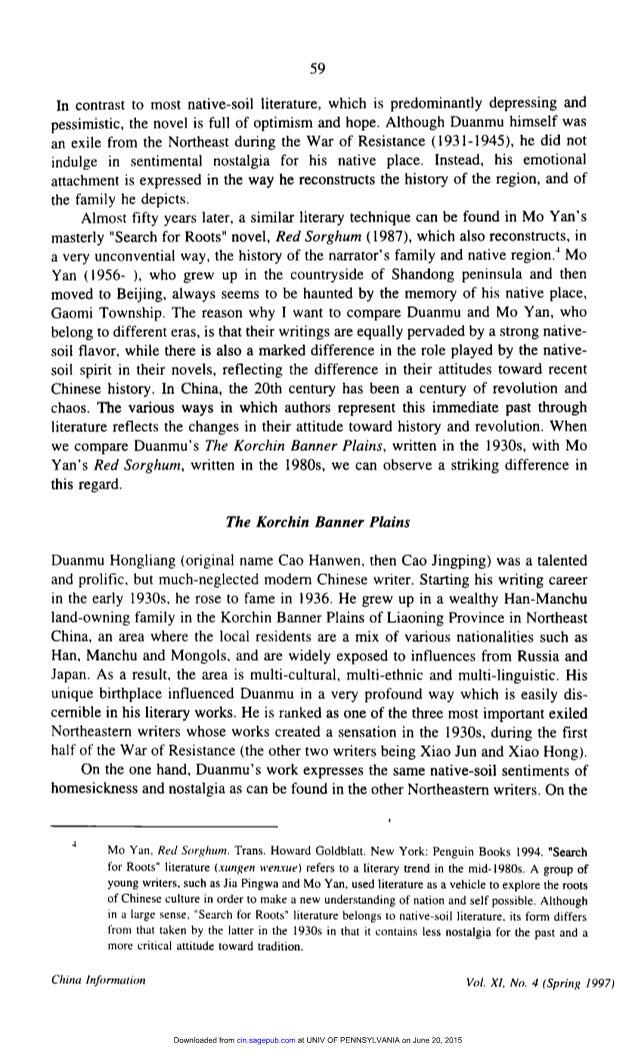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10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端木蕻良和莫言虚构世界中的“乡土精神”
1935年,鲁迅首先提出了“乡土文学”这个词。他接着解释道:“那些住在北京并写下自己感情(对他们的家乡)的人,不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是乡土文学作家”。然而,他继续补充道,“在写乡土文学之前,[作者]可能已经被他的家乡放逐,被迫迁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因此,他必须把意识中的lsquo;父亲的花园rsquo;带回来,这样的花园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也许回想起已经在自己的家乡上灭亡的东西比思考现实中仍然存在的东西让人更舒服或更安慰。”
一个人对从前的家乡和永远失去的东西的怀旧是乡土文学中表达的关键情绪。这种怀旧情绪与中国知识分子最初的抵抗倾向,或者至少是在五四运动期间和之后对现代性的一些抵触情感有关。田园诗般的农村生活不可避免地由于城市邪恶的入侵而崩溃,这是许多乡土作家的主题,如沈从文,王鲁彦,甚至鲁迅本人。
端木蕻良最重要的小说是写于二十世纪30年代的《科尔沁旗草原》,其中却表达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与大多数主要表现沮丧和悲观的乡土文学相比,这部小说充满了乐观和希望。虽然端木在抵抗运动(1931 - 1945年)期间是东北的流亡者,但他并没有沉浸在对家乡的感伤怀旧之中。相反,他通过重建该地区历史以及描绘家庭的方式来表达情感。
近五十年后,在莫言的“寻根”小说《红高粱》(1987)也发现了类似的文学技巧,它以不寻常的方式重建了叙述者家庭和本土地区的历史。在山东半岛的农村长大,随后搬到北京的莫言(1956-)似乎常常被他的家乡——高密乡的记忆所困扰。我想把属于不同时代的端木和莫言作比较的原因是:他们的作品同样渗透着乡土气息,但乡土文学的精神却在他们的作品中却有着明显差异,这反映了他们对中国近代史的态度差异。在中国,二十世纪是革命、混沌的一个世纪。作者通过文学的各种方式反映了他们对历史和革命态度的变化。当我们把端木在二十世纪30年代撰写的《科尔沁旗平原》与莫言在20世纪80年代所著的《红高粱》作比较,就可以观察到这方面的差别。
科尔沁旗平原
端木蕻良(原名曹汉文,然后是曹京平)是一名有才华,高产,但被忽视的现代中国作家,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写作生涯,于1936年成名。他在中国东北辽宁省科尔沁旗平原的一个富裕的满汉家庭中长大,当地是由汉族,满族和蒙古族等不同民族的居民所形成的混合区,而且还受到了来自俄罗斯和日本的影响。正因如此,该地区是多元的,多民族的,多语言的。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特殊的出生背景深深影响了端木,其作品创作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也就是抵抗战争的前半期,而他也被列为三大流亡东北作家之一(另外两位作家是萧红、萧军)。
一方面,端木的作品表达了与其他东北作家相同的乡土情结和怀旧情怀。而另一方面,他是一个非常特别以及个人主义的作家。在专题关注、文学风格和语言的使用方面,其作品是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主义的混合物,这明显地使他脱离了同时代人。
科尔沁旗平原的故事是从二百年前开始的,当时一群人从山东半岛的洪水中逃脱,成为了科尔沁旗平原的先驱者,并于1931年,抵抗战争的前夕结束了。作者重点描绘了最先从山东逃难的丁氏家族的兴衰。在前三章中,描写了丁氏家族是怎么渐渐走向强大与富有的。接着丁宁就出现了,他是一名经过三年的学习,从南方回国的十八岁的西方自由主义学者。从这起,他便成了故事的核心。虽然他对家人和家乡确实有一些情感,但也对家庭的衰落越来越失望。他同情农民,尤其是那些陷入贫困的和被压迫的女孩。最后,由于没有成功处理家族企业和反叛的农民,他必须离开家园去寻求新的生活。
与他的故事成平行的人物是大山,他的母亲是丁宁父亲的第一任妻子黄宁的妹妹,大山是反对丁氏家族的反叛农民的领袖。在小说结尾,他正处于成为一个民族英雄的边缘。
同传统的史诗文学一样,端木以小说中的大灾难为始,叙述的第一重要层面就是该地区历史悠久的“起源”及其早期的居民。正如叙述者所说,“记忆中的传说,是白鹭湖居民心中难忘的悲惨记忆,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第1页)。这个传说已经困扰了该地区许多代人们的回忆,并且由于长时间的口头相传,已经有了强烈的神话色彩。“在古代文学中,”巴赫金说,“这是记忆而不是知识,是创造性冲动的根源和力量。”虽然知识提供了一个事实的过去,记忆提供了一个有想象力的过去。诺斯罗普·弗莱在说记忆是“缪斯的母亲,激励着诗人”时也表达了这个类似的想法。在中国文化中,这种传说,追溯家谱或揭示过去的秘密,不管是明确的还是隐含的,往往都是一种延伸的祖先崇拜。
科尔沁旗平原是钟覆灭也是重建,是痛苦也是希望的传说。它开始于二百年前山东半岛的洪灾,造成数千人死亡,摧毁财产和庄稼,并从他们的家乡赶走了一群幸存者,迫使这群人走向“东北的神秘平原”(第1页),“野蛮人”的未知领域。叙述者似乎有意识地提到了圣经中的洪水故事,当他在描述不幸的难民时,用了“被上帝驱除出伊甸园的蛇”这一比喻(第1页)。经过一连串的灾难,饥饿,瘟疫和死亡,疲惫的幸存者终于到达了一个荒芜却富裕的土地,代表着希望。这个传说在原本小说结构的基础上开创了破坏—建设—破坏—建设的主题周期。
第一次的破坏是洪灾及其可怕的后果。一方面,该地区的人民对于大自然的破坏性暴力是无能为力的。但另一方面,由于移民开辟了新的途径,破坏也带来了机会和希望。因此,人类与自然之间可怕的、对抗性的洪灾,通过人类和宇宙的和解,最终也开始了一个新的、和谐的进程。第一章中集结的受害者祈祷天堂怜悯的壮观景象,生动地表明了他们想恢复与天堂/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
在埋葬了刚死亡的两个强壮的年轻人之后,大家在空地上围成一个个圈子,紧靠着彼此跪下来,开始向天堂祈祷。[...] 棕色的泥土被紧紧地压在地面上,饥饿的人空着肚子,即使野草也把头靠在地上,不再抬起来。一切都从恐惧和害怕中沉寂下来,只有祷告的话语和蜂拥的苍蝇才可以到达群众的中心。[...]突然有一个女人失控,变得疯狂。数以千计的人立刻从地上抬起头,有些惊讶,恐惧,难过以及不知所措。(第12页—第14页).于是他们要杀死十个处男处女作为祭祀品献给天堂,这时一个名叫丁的神圣先知戏剧性地出现了,阻止了杀人并且赢得了人们的信任。老先知把这些人带到他们的新家。据叙述者说,“甚至是瘟疫也吓坏了,看到他们已经到达了广袤富有的土地——科尔沁旗平原,就停止了杀人的行为”(第17页)。
传说增强了那位让丁氏家族走向富有和强大的先知的神秘感。在传说中,他和一位年轻的狐狸仙女结婚了,而且拥有风水的特殊知识。这两个神秘因素有助于解释他神圣的预言能力,更重要的是为他后裔的财富提供了合法性。丁的出现把第一层处理的区域历史和第二层涉及到的国内历史联系到一起。在循环的叙事结构中,他把人们从破坏阶段带到建设阶段,这一过程持续了将近二百年:在该地区进行种植,丁氏家族慢慢地富有了。
循环中的第二次破坏是发生在当代,这是小说的中心情节,正如第四章的标题所示:“这是我们故事的真正开始”(第94页)。在科尔沁旗平原的普遍危机中,场景转向了丁氏家族的衰落。丁氏族的颓废的生活方式和不善的经济管理模式造成了第二次的破坏,愤怒的农民进行了反叛,当地的土匪和日本士兵进行了施暴。
在第三章中已经传达出了丁氏家族注定的命运,在一场极具戏剧性的场面中,俄罗斯士兵强奸了大山的母亲以及丁宁父亲的第一任妻子,而丁宁的父亲把她们从死亡中解救出来。第三章的标题——“另一个邪恶的触角”表明:自然不是造成区域和国内危机的唯一破坏力量。随着场景从神秘的传说转变为当代人的生活,在人与自然/天堂的冲突之后,我们现在面对人类之间的矛盾时,自然起初是以洪灾以及及其后果的形式出现的不人道的力量,现在却被描绘地比人类社会本身更加公正和人性化。人类之间在进行生死攸关的斗争的时,大自然被看作是正义的象征。这是一种拟人化的神学,为穷人和弱势的人们提供保护,带领他们进入森林和未开垦的草原。然而,当自然法则受到侵犯时,它会用雷电和可怕的地震来表达愤怒和惩罚罪犯。
对比
就同端木把科尔沁旗平原的名声提升到国际一样,莫言也把山东半岛高密县的名声提升到了国际。由于对景物的生动描述,以及其浓厚的神话和乡土气息,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为“寻根文学”的领先人物。
他的《红高粱》描述了东北高密乡的一个家庭的历史,它跨越了二十世纪的三代人。叙述者“我”,是寻根人的孙子。他似乎从一开始就有兴趣去找出他祖先没有讲过的故事,于是叙述者回到自己的家乡调查和重写家族史。狭义上说,这可以被认为是祖先崇拜的延伸形式,但也表现出对现有历史的不信任倾向。这与端木的《科尔沁旗平原》类似,他的故事主要是以记忆为基础,如口头的传说:从“一九九二年的一位老太太”到“竹子的伴奏”(第十三页)。在莫言的小说中,“起源”并没有端木的“逃避”洪灾那么壮观─也不是逃脱自然灾害,莫言的主角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由人类造成的困境中生存。正如丁氏家族在科尔沁旗平原上找到避难所一样,所以莫言的角色在东北高密乡神秘的高粱田里找到了自己的“诺亚方舟”。
端木和莫言都关注人与土地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端木的科尔沁旗平原和莫言的山东东北高密乡的高粱田不仅自身惊奇,神秘,而且也是一个相对而言人性化的地狱,为其居民提供重要的能量来源,使他们在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可以采取行动。
在端木的小说中,土地的形象与大自然的抽象概念相融合。在人与自然(洪灾)的第一次冲突中,自然是神化的。而第一章崇奉天堂的神圣仪式之后,自然与人类之间似乎已经建立了新约。科尔沁旗平原的土地似乎是天上的礼物。在小说结尾,激动人心壮观的黎明景象预示着日本入侵,内战即将来临的新灾难。一方面,大自然反映了即将到来的混乱。但另一方面,大自然也指出,由于这场混乱,人民群众开始觉醒,他们共同对抗灾难去建立了更美好的未来。最后的场景中,在日出的过渡时刻描绘了澎湃的海洋,兴奋的民众,提供了强大的效果─人与自然的融合,创造出新的整体,新的宇宙。
自然直接影响了人的精神和品格。丁宁是一个孤独的人物,唯一陪伴他的是自然─在许多场合,他的独白实际上是与大自然的对话。当他扫妹妹的墓时,他可以听到来自草原的抱怨声,“受伤与压迫”(第150-51页),这引起了他一连串的哲学思考。丁宁认为,“只有这广袤的科尔沁旗平原才能给人以宽恕,诚意和怜悯hellip;hellip;一种忧郁的感觉”(第155页)。每当他靠近平原,丁宁都会感受到自己心灵的激荡;他相信它们以灵感和勇气培养他,塑造他的个性。他说过一点:“只有山水可以使人类健康,只有当人们遇到大山时,人类的世界才能壮大”(第155页)。
同样,红高粱的所有英雄都离不开东北高密乡的富饶。正如端木和莫言,表明了自然的野性和人类的原始冲动是能够重塑社会结构的变革力量的来源。例如,叙述者的爷爷是这个时代的真正英雄,由于他从高粱田中获得无限的生命力,因此比该地区的任何政治力量更真实。此外,对于端木和莫言,土地的野性在人们身上产生了强大的力量,使他们超越了所有的社会公约和世俗的规约。这引起了丁宁对世界的哲学思考:爷爷忽视道德规范的自由的行为,以及奶奶在谋杀她的合法丈夫的基础上还可以经营酿酒厂的能力。而端木全心全意地赞扬自然野性。在莫言的《红高粱》中,叙述者关于他家乡的感受是混合的,甚至是矛盾的。“我已经学会了全心全意地爱东北高密乡,肆无忌惮地去讨厌它[...]东北高密乡很容易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最丑恶的,最不寻常的,最常见的,最神圣的,最腐败的,最英勇的,最卑鄙的,最难爱上的地方[...]它预示了魅力,激情和爱,这是动荡的。”
对于端木而言,自然是一种神圣而超越的力量,有时候像母亲一样柔软,有时像暴风雨一样的残酷,对于莫言,这更多的是朴实,这是具体可见的工作空间,人们可以在土地上耕种并享受它的回报。特别是该地区的高粱酒体现了以纯粹的形式提升乡土精神,充满了勇气和灵感。端木和莫言对自然的不同构思方式也决定了他们对人物的写作方式的不同。在端木的世界里,相对于自然的强大力量,人类似乎是受限的和被动的。在《科尔沁旗平原》的开篇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场面,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祈祷食物与慈悲,这也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无奈和脆弱。相比之下,莫言笔下的人物不是脆弱的,依赖的。他们生活的主要目标仅仅是生存,他们从原始的激情,如爱和仇恨中,获得重要的力量和精力,这使他们很主动。《红高粱》中的乡土精神,不仅将他们从传统习俗里解放出来,而且将他们与自然界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其可以超越世俗的境界,克服一切困境。因此,在张艺谋电影《红高粱》中,葡萄酒厂的工人不向天堂祈求获得帮助去打败敌人,而是每个人站在葡萄酒神殿的前面端着葡萄酒, 似乎向上帝保证,他已经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勇气去打败敌人─那些违反了自然法则。使用高粱田作为执行地的日本士兵。
端木与莫言的另一个区别是:前者以宗教方式处理土地与人之间的联系,后者完全归到这两者的结合。端木在《科尔沁旗平原》开始时提到的“起源”,从对祖先崇拜的角度来表示对先驱的尊敬。相比之下,莫言小说中的人物,通过高粱酒,从土地上获得了自发性。他们去爱,去恨,大笑,喝酒,寻求报复,而不用担心传统的儒家道德。正如叙述者所说的,他的奶奶,九儿,“她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因为她是抵抗的英雄,性解放的开拓者,妇女独立的模范”(第14页)。
可以肯定的是,端木的小说有提倡反叛的态度,但在小说中,只有两种无效的形式:一个是丁宁的思想,一种不会产生有效行动的无止境的思想;另一种是大山的形象,他只是农民革命的潜在领导者。端木的希望仍然集中在一场政治革命上,而莫言却蔑视政治,只钦佩农民的自发性和活力,他们的激情以及大胆的行为都是源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5201],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以上是毕业论文外文翻译,课题毕业论文、任务书、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