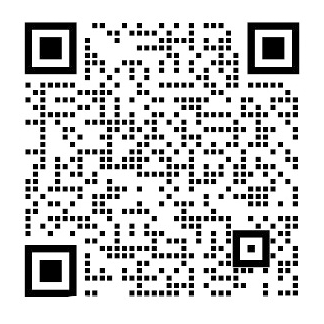EMERGENT CHINA AND CHINESE: LANGUAGE PLANNING CATEGORIES
JOSEPH LO BIANCO
(Received 28 July 2006; accepted in revised form 20 November 2006)
ABSTRACT:This article extends a taxonomic system initially developed by Kloss to describe constitutional and more broadly legal-political categories for language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Chinese situation. The article extends the taxonomy of spheres of language planning action from sovereignty and jurisdiction to include influence, acquisition, and retention and recovery. These categories are applied to the wide framework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Chinese that is following in the wake of the vast expansion of the economic and the emergent geo-political presence of China. The taxonomy is used as the basis for discussion of the articles comprised in this special issue of Language Policy whose content and key arguments are incorporated in the present article.
Introduction
In recent years commentators all around the world have spoken of lsquo;the emergence of Chinarsquo;. This volume addresses what some have termed lsquo;the emergence of Chinesersquo;. Of course China and Chinese havenrsquo;t “emerged” in any literal sense, even to outsiders. The reference is to the new prominence of China in world affairs, and if we are to be true to history we should say Chinarsquo;s recovered prominence in world affairs, until very recently dominated by a westernized modernity. The re-emergence of China, and therefore of Chinese, might therefore be more apt. While what counts as prominence is all too Language often reduced to measures of the quantity of exchange in goods and service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trade volumes often operate as a proxy for soft power (Nye, 2004). Contemporary consumerist culture links commodity production with trans-national cultural and even political influence. Emergence also suggests a future presence for Chinese in what is researched and exemplified in discussions about the communication profile of the world, but also within the language professions, such as those addressing language education, applied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policy, in places far from China itself.
The 1990s saw the rapid expansion of Japa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essentially a delayed reflec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emergence of Japan in the preceding two decades. The 1990s, however, has seen the dramatic commercial expansion of China, especially in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increasingly in trade. Attracting vast quantities of foreign capital into its industrial and tertiary markets has helped stimulate Chinarsquo;s impressive economic performance which has grown at double digit rates unabated since the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of the late 1970s. However, unlike Japanrsquo;s reluctance to match its newfound economic power with geo-political presence China appears likely to assume the big power role its UN Security Council status, population size and military strength make possible. In addition, China has long been lsquo;projectedrsquo; globally by the physical presence of inter-generationally vibrant, Chinese speaking and China-identifying communities in many parts of the globe. This spread of authentic community-level Chinese-ness also gives several varieties of Chinese a greater range and geographic reach than other Asian languages.
The dominant European languages attained their inter-continental spread on the basis of centuries of political colonizing. However, as Eco (1997) points out, English is unique among the European sourced lingua francas because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transfer of global dominance from Britainrsquo;s empire to Americarsquo;s economy was achieved within the same language. No previous power succession where one dominant world power succeeds another has been achieved with both using the same language. This maintenance of language was accompanied by a major change of the modality for hegemony, so that influence is more prominent in the exercise of power prompting vibrant reconsideration from normative political theorists of the left, right and center about how to characterize and account for the new meanings and contemporary forms of “empire” and “domina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globalization, the decline of exclusive sovereignty and increase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Hardt amp; Negri, 2001; James, 2006; Maier, 2006). In Hardt and Negrirsquo;s (2001) estimation we now have Empire without imperialism, under conditions easy to recognize but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Although language attraction (its material utility and cultural capital), cannot be solely explained by calculations of commerce and hard power, as though language spread is the soft-power repercussion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 historical precedents suggest a strong relationship.
While it is unlikely that Chinese can attain the geographic dispersion of English, French, Spanish, and possibly not even that of Portuguese, all of which have many sovereign state powers sustaining the continual elaboration of these languages, all the while forging polycentric norms of correctness for the languages, none of this precludes Chinese from any conceivable domain or institution. In addition the ethnic Chinese networks, family and region based rather than ordered by sovereignty and jurisdiction, nevertheless already constitute a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diaspora. The lag of one to two decades between the emergence of Japan to the emergence of Japanese as an educational commodity is being repeated with China and Chinese but with the addition of a more widespread and communicatively vibrant speaker community.
Predictably, Chinarsquo;s economic success, epitomized now in talk of its emergent superpower status since the latter part of the 1990s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new millennium, has stimulated phenomenal expansion i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Chinese. Although strongest in Asia it is becoming evi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新兴中国与中文:语言规划范畴
JOSEPH LO BIANCO
摘要:本文扩展了克洛斯针对美国的汉语情况所做的一个专门描述语言政策的宪法及广泛的法律政治范畴的分类系统。本文将从主权和管辖权,包括影响,收购,保留和恢复来扩展语言规划领域的分类。这些类别被广泛应用于学习和教学的组织机构,是随着巨大的经济扩张和新兴的中国政治而产生。该分类是讨论本文的基础,包括这个特殊的语言政策问题的内容和关键参数均纳入本文。
简介
在最近几年,世界各地的评论员都谈到了“中国的崛起”。本卷涉及了一些所谓的“中国的崛起”。当然,中国和汉语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出现”,甚至是对于外国人来说。如果提及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新突破,我们要尊重历史因此应该说中国在国际事务被西化的现代性占据主导地位之前已经有突出表现了。由于中国的重新崛起,汉语的崛起也随之而来。而衡量一个国家的突出表现往往都是通过减少对商品和服务的交换量,这在当代世界贸易中往往作为一个软实力的代理(Nye,2004)。当代消费文化的对商品生产与跨国文化乃至政治产生影响。这个“崛起”暗示了目前中文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并谈论了世界的通信概况,以及在中国边远地区的语言领域的问题,如解决语言教育、应用语言学、语言政策。
上世纪90年代日语教学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张,日本在过去二十年在全球经济中突出表现,本质上是一个滞后的反映。然而,90年代以来,已经看到了中国商业的巨大扩张,尤其是在工业生产和贸易中。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进入其工业和第三市场,这有助于刺激中国可观的经济现象,这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自由化之后,其经济表现依然不减。然而,与日本不愿意将新出现的经济实力与地缘政治存在相匹配,中国有可能承担起其联合国安理会地位、人口规模和军事力量的主要角色。此外,中国一直在全球范围内以充满活力的跨时代的形象被“提及”,在中国周围的国家以及地球上很多地方都有人说中文。这种真正在邻国的中文传播使得一些中文种类的传播比其他亚洲语言达到一个更大的范围和地域。
占主导地位的欧洲语言在政治殖民世纪时已达到洲际传播。然而,就像艾柯提出的那样(1997),英语是唯一的来自欧洲的通用语言,二十世纪中期由于英帝国对美国的经济统治,实现了使用同一语言。一个主导世界的力量成功地使另一个没有对先前的权力进行继承的国家使用相同的语言。这种语言的维护是伴随着霸权模式而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因此,促使充满活力的激进政治理论家去重新考虑权力行使造成的影响显得更加突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对“帝国”和“统治”的新含义和现代形态进行了描述和解释,专属主权的衰落与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根据哈特和内格里的(2001)估计我们现在有帝国而没有帝国主义,在这种条件下容易辨认,但很难理解。虽然语言的吸引力(其物质功利价值和文化资本),不能完全由商业计算和硬实力来解释,尽管语言传播是政治和经济软实力的反响,历史先例表明这之间的一个强有力的关系。
虽然这是不可能的,中文的普及可以达到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甚至是葡萄牙语的地理分布,这些国家都具有许多国家主权以此来维持对这些语言的不断扩展,而这些国家都在规范多中心的语言正确性,这些都不妨碍来自任何可能的领域或机构使用汉语。此外,华人的网络是家庭而不是基于区域主权和管辖权的命令,尽管如此,已经构成了一种有效的交流。日本作为一种教育商品被重复这是二十多年来的一种滞后表现,但中国及汉语的崛起之间却有更广泛的和充满活力的汉语使用者。
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经济的成功,成为上世纪90年代后期树立新兴超级大国地位的典范,在新千年的最初几年刺激了汉语在教学和学习中显著的发展。虽然亚洲最强的教育系统其更远的目标是“把握现在”的几个关键的中国教育和文化机构,鼓励世界各地的人学习中文。(罗比安科,林奇,与雷霍里克,2006)。
汉语语言规划
最近,中国的语言政策和规划都强调了一直缺乏关注的问题,即致力于在中国的语言习得规划这一复杂的问题。代表中国人、在中国的侨民和中国全新的人群专门研究分析语言的促进。
在欧洲的一些语言政策分析可获得语言审查,在中国语言教育规划中关注学习的脚本,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的教学,和英语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一些作者把最近英语进入中国的需求归于2001年12月11日世界贸易组织申请的15年后的需求,以及常不受重视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其他作者还补充说,2008年主办夏季奥运会的北京,刺激了大量的英语学习。我国第二语言写作的关键领域包括英语的中文变体,或身份和英语大众文化研究的考试。从社会学角度看来,中国走上了自己的道路就像Pakir提到的新加坡,称为“懂英语的双语政策”。 (参阅林,2002;启平王树柏,2002)
中国社会内部无处不在的变化,引起了包括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开放,被视为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包括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个人身份的挑战(亚当森,2002;高,2004)。
本书旨在通过分析中国对特色语言教育政策研究的贡献,特别是在中国大陆之外进行的汉语教学,中国的迅速崛起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中国崛起的规模,和其历史的深层意义正在走上一个新的地位,令LPP分类系统意识到在汉语特色的情况下一个潜在的“新英语”的发展。“hellip;世界最大的语言工程项目在中国hellip;”(周、罗斯,2004:1),与宿主语言政策2000多年来,仅包括在目前的分类系统中并作为一种来源,本卷只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的文章。
这个分类系统基于重叠的语言政策和规划领域的概念。这个系统有5个组成部分,分为管辖权,主权的领域,影响,保留和恢复,并采集。这些领域的语言政策和规划的活动旨在反映人类意识的范围和计划的活动与语言:最明显的是学习和教学,但最终也是法律管辖和政治主权的活动,治理教与学的制度体系。本LPP活动系统分为五个范围的有知情选择和包含本卷中的文章
LPP的范围
海因茨kloss在开创性的美国语言政策的历史研究(1998)中区分了美国语言规划领域之间的“管辖权”和“主权”。 在以前的工作中(罗比安科,2001),扩展了克洛斯的包括“影响”范围的二分法(理解为说服和宣传)。国家的语言推广政策,通常是国家文化政策的一部分,是LPP影响范围内最制度化的形式。
在本文中这种LPP范围的分工领域进一步延伸到了包括通过增加保留和恢复的五个部分的方案,是中国华人社群在海外语境中的努力与“习得”, 库柏(1989)说这是传统的外语教育规划,了解其主要是作为一个自上而下的规划过程。LPP行动的五个领域如下。
(一)管辖权
克洛斯的管辖权原则描述了在LPP活动内完全纳入美国政体的48个州(这样的宪法是有效的没有限制),在一些独立的领土中完全没有模糊的宪法管辖范围。在费施曼(1972)早期的概念化语言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文化活动;与国家的服务、建国活动)三大方面。首先,语言的功能是作为文化正宗的标志;其次,是作为政治统的工具;第三,是作为行政效率的手段。克洛斯使用LPP行动范围的可靠性,统一性和效率性都是由一个合法的政治权威的首要管辖机构所制定的。
这个主要概念应用于中国,作为政策指导原则的管辖权是指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争议领土法规效力的规定。在传统的LPP的地位规划部分是基于这一原理(DeFrancis,1984;周太阳,2004)。典型地说,这一传统的工作描述了中国语言的历史发展,中国的各种关系,代表或反对语言种类的国家措施,以及对民族语言的公众和机构识别的规定。因此,司法管辖权需要设定,语言是国家的财产,“民族语言”一词是有意义的,因为语言是国家行政管理的工具(需要标准化和可复制性的形式),作为文化依附与归属的象征。
然而,也许在中国最突出的设置是正字法习俗和变化的分析,包括历史悠久的拼音政策,显然限于合法管辖权和领土。事实上,区分LPP在设置上超出东亚和东亚,戈特利布和陈(2001:5)指出,“剧本和书面语言的改革通常是第一个春天的语言规划者和一般公众的头脑”。 事实上,从1954年起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官方机构被称为中国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只有在1986年被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陈,2001a,b)。2001通用语言文字法也明显在这方面给予所有的法律条款问题的渗透(41–Rohsenow,2004:43)。
(二)主权
克洛斯说,主权领土范围是指我们在安全保护伞下的政治或法律条款,及赋予的地方自治。在中国语境下,这种定义包括的领土是在中国管辖的一个最终的法律政治意义下的而不是即时中国主权下的。香港是这种状态的最明显的例子。
从英国的专属管辖权的转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SAR)。在1990年4月4日由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1997年生效。这个基本法取代了英国的专利和皇家指示下的前宪法条文。香港基本法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在1984年12月19日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下起草的。在中国部分地区,这个特殊的行政区域地位给“一国两制”原则带来了影响。
类似的情况是澳门1999年将政治管辖权从葡萄牙转移到中国。在这两种情况下,当回归中国的司法管辖权发生时这一主权仅限于50年。
也许,这样的过程和安排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管辖权的重叠,及受到模棱两可的解释。法律解释制度,与现实政治的力量,用于解决歧义时,他们变得非常大甚至成为政治问题,但在实践中,一些模糊性使得实际的政策制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在重叠政治话语的时代(影响范围、说服和推广)提供线索,无论何种模糊和冲突将最终得到解决。
(三)影响
一个势力范围的加入使LPP实践进行更加细致入微的社会化分析,这涉及到一个连续的活动推广和吸引力。随着中国越来越吸引广泛的社会和文化成行力,它为自身的语言合并产生了一个几乎自动的需求。教育部在正式的职责外,明确了中国巨大的经济成就,中国的“崛起”与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至少在亚太地区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最终在全球达到吸引独立的政策势头。
一个很好的例子,2005年7月12日亚洲社会的新闻发布会声称这样的地位中包含纽约(亚洲社会,2005)。有无数的小标志,如在线和意大利主要晚报印刷部分,Il Corriere della Sera提供中文读者摘录的文章,直接关系到澳大利亚的矿产和能源资源的繁荣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加入了自己独特的一种“软实力”来应对明显的“硬实力”(奈,2004)。
影响力最大的制度化和战略形式是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机构肩负着促进海外的民族语言文化发展这一任务。大约10年后,日本和韩国完全成为成功的贸易经济体,他们分别为外国代表建立国家文化机构和委托这些机构主要行使语言传播功能。日本基金会于1972年成立,最初设立在外交部之下,很快就走上了文化交流的发展道路,在海外设立语言学校,提供助学金和奖学金,赞助文化旅游,开展日语水平测试、教学材料和支持各种各样的教师活动。
韩国基金会成立于1991年,也是一个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语言和交流活动阵地。同样,在1987年中国成立国家对外汉语教学小组办公室(国家汉办)与一系列的活动,包括汉语水平考试(HSK)、文化交流和旅游,为中外教师提供网络支持,以及一系列的教学支持。近年来一个重点是在国外建立合资语言中心,孔子学院。
(四)保留和恢复
在汉语为目的语的情况下,移民社区体现了对代际语言的保留和对现代标准汉语(普通话)的合并,而且随着对语言能力丧失或削弱的恢复是LPP一种自下而上的指导性措施。LPP的范围体现了在许多设置方面语文教学的复杂性,要求教师要适应双语和多语语境、衔接课程的方言和在多种语言规范之间偶尔出现的不同观点。情感和身份问题,有时体现在借助上下文语言来谈判和辩论,在其他情况下,由来源国官员讨论过程并做出的决定是少有问题的。
许多国内政策对语言的影响都来自对语言混合和语言转换的各个阶段的实际情况,与预先存在的和充满活力的方言相结合意味着谈判,在围绕规范和标准的背景下,为移民设置的“普通话”问题结合起来时,身份和家乡的规范是中国现在正在通过的范围中的一部分。
然而LPP通过邻国汉语使用者为移民提供持续的学习动机和习得兴趣以及使用目的语的能力。新加坡对方言变化和标准的规范,为代表讲华语运动提供的证据表明,与当地社区管辖说话人的语境与在台湾争议中更政治化的设置和当地语言复兴思想领域管辖权的重叠相结合(史葛和那本,本卷)。
(五)合并
这是社区代际语言习得的保留和恢复。当代美国对汉语的促进政策(亚洲社会,2005;王,本卷),和澳洲历届政府对亚洲的语言政策这两者强有力地证实了这一观点(罗比安科,2004;2005a,2005b)。LPP的范围有着自己丰富的文学概念,但这些都不是经常与常规LPP有联系的,但更依赖于教育政策或应用语言学和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语言习得计划的近因作为一种传统语言规划理论的认证揭示了随后出现的社会语言学的起源,民族主义、民族共同体和移民问题是研究兴趣的主要领域。然而语言合并甚至在今天的语言规划理论中往往更多的致力于少数民族语言或第二语言教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教育进社区的广泛实践。这一分离体现在谁研究什么,以及不同的研究小组是使用什么工具分析的。
主流文化实践的语言政策和规划的研究日益突出,但仍倾向于有轻微不适的应用语言学会议,看到他们的自然家庭教育研究会议。然而,主流文化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对于汉语,甚至在一般情况下对文字和非字母书写系统,语言规划理论的确是政策和教育实践分析的资源中心。
结束语
划分政策空间为五个部分以及分析汉语教学,根据这些观点在不同的设置内提供了在一个广泛的教育环境中理解当代中国的命运。它也产生了关于描述这些设置的趋势和结果的一系列的问题。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30362],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