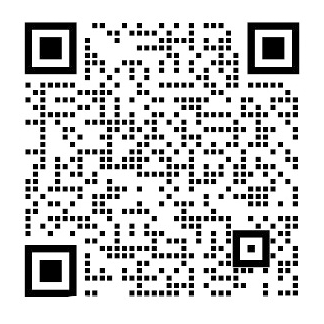文献翻译原文
Extracted from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 Language Variation, Cultural Models, Social Systems, which is edited by Gitte Kristiansen and Reneacute; Dirven. Gitte Kristiansen is the chairman of Spanish cognitive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and the executive editor of Application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e excerpt is from the first page to the eighth page.
Introduction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Rationale, methods and scope
1. Why do we need a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Nine years ago Langacker (1999: 376) programmatically emphasised the necessity of extending Cognitive Linguistics to the areas of discours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rticulating the dynamic nature of conceptual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 leads us inexorably to the dynamics of discours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While these too have been part of Cognitive Grammar from the very onset, they have certainly not received the emphasis they deserve.
In a similar vein, a series of scholars whose research likewise falls within the disciplin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have in recent years repeatedly advocated the need for approaches which would bring the objects of study and the methodologies employed in sociolinguistics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closer together,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se researchers have taken important steps in the direction of an empirically validated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ocial dimensions of linguistic vari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millenium, in other words, a heightened awareness regarding the social aspects of linguistic variation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necessity of implementing even developing the right methodological tools on the other hand, match an already existing trend of research. For examples of descriptively and methodologically oriented studies, see many of the contributions in Dirven, Frank and Puuml;tz (2003), Dirven (2005), Geeraerts (2005), the theme session on lectal categorization and lectal variation celebrated at ICLC9 in Seoul, and the theme session on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at ICLC10 in Krakoacute;w. On a more programmatic level, see Sinha (2007) on language as an epigenetic system, Zlatev (2005) on situated embodiment, Itkonen (2003) on the social nature of the linguistic system, Croft (forthcoming) on social interaction, Verhagen (2005) on the role of intersubjectivity, Harder (2003) and Bernaacute;rdez (2008) on typology, variation and cognition. We can thus now rightfully speak of a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This volume testifies of such rich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work and gives proof of an already vigorous cognitive-sociolinguistic strand inside the wider Cognitive Linguistics paradigm.
Four decades ago, William Labov objected to the term “sociolinguistics” on the grounds that there could surely be no way of doing linguistics which did not at the same time take social dimensions and social variables duly into account. Hence, the new term was thought to be redundant. Y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a model in which usage-based and non-modularity are key words and which thrives more than most other theories o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the inclusion of the term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 is far from arbitrary. There are many good reasons why the type of studies included in the present volume should be brought together under the same descriptive heading. Let us mention just a few of them.
In the first place, as we just pointed out, the volume brings together various approaches from a burgeoning but still fragmented area of research. As such, it coins at the level of book title what is already a practice in several established schools and, in a less condensed and more scattered manner, in many other academic environments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The volume will serve to show commonalities between these approaches and help those present and future scholars who embrace a socio-cognitive conception of language to better situate their research and to define their work in more precise terms.
In the second place, the volume—the first to bear the title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contributes to establish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link between sociolinguists and practitioners of CL. In fact, we very much hope that the content will be equally appealing to sociolinguists and cognitive linguists. It is not uncommon to engage in conversation at a conference with scholars with a specific interest in cultural linguistics or sociolinguistics and discover that the term cognitive linguistics is still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first generation (i.e. Chomskyan) cognitivism—and hard as one may try to explain the fact that the two disciplines share little more than the common denominator cognitive, these beliefs more often than not turn out to be very deep-rooted. Conversely, those scholars who are anxious to see how social variation is dealt with in grammatical theories that take an inherent interest in cognitive processes and contextualised
meaning, and which cannot commit themselves to the Chomskyan belief in the homogeneity of language, have unfortunately so far not had access to a representative volume. This survey of current research and possible inroads will hopefully serve to bridge the gap.
In the third place, it is firmly believed that Cognitive Linguistics itself will unescapably benefit from turning its attention towards variational and interactionist linguistics. For a start, there is still a widespread tendency with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towards studies based on the written production of standardised varieties, but a truly usage-bas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nnot ignore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variation to be found within the standard and non-standard varieties of a language. It cannot afford, in other words, to work around language at the almost Chomskyan level of homogeneous speech communities. A usage-based linguistics takes language as it is a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文献翻译译文
节选自《认知社会语言学: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范围》,这本书是由吉特.克里斯蒂安森和德尔文编著的。吉特.克里斯蒂安森是西班牙认知语言学协会主席,也是《认知语言学的应用》系列丛书的执行总编。下文的翻译节选自该书的第一页至第八页的内容。
引言
认知社会语言学: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范围
1.我们为什么需要认知社会语言学?
九年前兰盖克(Langacker)(1999:376)计划性地强调了将认知语言学扩展到言语交谈和社交领域的必要性:要阐明概念和语法结构的动态本质,我们必须进行言语交谈和社交动态性的研究。虽然这些也从一开始就是认知语法的一部分,但它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同样,许多学者的研究也停滞在认知语言学范围内,这些学者近年来一直主张采用其他方法,将研究目标和方法论应用到社会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当中,从而使其更加紧密的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者在语言变异社会维度的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换句话说,在新的千禧年开始时,一方面人们对语言变异的社会方面的认识提高了不少,另一方面,完善甚至发展正确的方法论工具的必要性也显著提高,这恰符合目前的研究趋势。有关描述性和方法论导向性研究的例子,请参阅德温(Dirven),弗兰克(Frank)和普茨(Puuml;tz)(2003),盖拉茨(Geeraerts)(2005)的研究贡献,与语言范畴和语言变体相关的主题会议在首尔第九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上开展,关于认知社会语言学的主题会议在克拉科夫的第十届国际认知语言学大会上开展。更高层面的研究,有如辛哈(Sinha)(2007)将语言作为表观遗传系统的研究,兹拉特夫(Zlatev)(2005)关于位置实例研究,伊特科宁(Itkonen)(2003)关于语言系统的社会性质研究,克罗夫特(Croft)(即将出版)关于社会互动的研究,韦尔哈根(Verhagen)(2005)关于主体间性的作用研究,哈德(Harder)(2003)和贝纳尔德斯(Bernardez)(2008)关于类型学,变异和认知的作用研究。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以正确的方式来谈论认知社会语言学。这些研究证实了许多实证研究和理论工作的成果,并证明了在更广泛的认知语言学范式中存在充满活力的认知社会语言学因素。
四十年前,威廉·拉博夫(William Labov)反对“社会语言学”一词是因为在研究语言学的同时无法做到合理兼顾社会维度和社会变异。因此,“社会语言学”这个新词被认为是多余的。然而,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一种基于用法和非模块性的模型是关键,并且该模型比其他大多数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理论更为兴盛——将认知社会语言学这一术语考虑在内绝非武断。将目前研究范围内的社会认知语言学纳入同一个语言学研究标题之下,有很多个理由。让我们来列举几个。
首先,正如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本文将新兴的,但是仍然分散的社会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各种方法汇聚起来。就其本身而论,在书名的层次上创作,这已经在几所知名的学校进行了实践,并且在世界上许多地区、其他学术环境中以较不凝聚和分散的方式进行了实践。本文将显示这些方法之间的共性,并帮助那些持有社会认知语言概念的学者,在当前和未来的工作中可以更好地定位他们的研究并以更精确的术语定义他们的工作。
其次,本文首次冠用了认知社会语言学这一题目,这有利于在社会语言学家和计算语言学实践者之间建立一种跨学科的联系。事实上,我们非常希望本文内容对社会语言学家和认知语言学家同样具有吸引力。会议中与那些对文化语言学或者社会语言学感兴趣的学者交流是常有的,同时还会发现认知语言学这一术语仍然与第一代(即乔姆斯基)的认知主义密切相关,而且人们很难解释这个事实,即这两个学科的共同之处比认知共同点还要少,这些想法往往根深蒂固,很难改变。相反,对于那些学者来说,他们急于看到社会变异如何在以认知过程和语境化为研究核心的语法理论中得到解决,这致使他们无法认同乔姆斯基语言同质化的想法,同时不幸的是,这些学者也一直没能接触到相关代表性的书籍材料。而目前这项关于研究现状和可能性进展的调查研究将有望弥补这些空缺。
第三,研究人员坚信认知语言学向语言变异以及互动语言学方向的转变也会不可避免的使自身受益。首先,认知语言学仍然普遍倾向于基于标准化语体书面创作的研究,但真正基于使用的认知语言学不能忽视存在于一种语言中的标准和非标准语体中的定性和定量变异。换言之,它无法以乔姆斯基同质语言社区的水平在语言中运作。基于用法的语言学将语言视为真实的说话者在某个确切的历史时刻、真实情景中所使用的一种工具并以此作为其询问的基础。作为这一事实合乎逻辑的结果,认知语言学需要采用实证法来有效处理社会变异:这一方法符合传统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高标准,并且能够区分变异的社会类型和概念类型。正如盖拉茨(Geeraerts)(2005:168-182)所论证的那样,认知语言学不仅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社会变异系统性地出现在受到严格审查的原始语言数据中,而且不得不承认,系统处理包含不同社会维度变异的唯一方法,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可靠的实证分析。简言之,社会意味着经验,而经验意味着社会。
此外,基于使用的基础学科(如认知语言学)倾向于选择“语境”作为关键词,这很自然。毕竟,就像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它首先将将这一语境法视为一种语境重构反应,这是针对那些没有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语言,也没有从社会维度来考虑认知性的方法来说的。这些方法包括将生成论作为这种去语境化趋势的有力说明,并采用不那么突出但仍然有力的方式——结构主义。语言,言语二分法为某种社会概念留下了空间,但它并没有处于语言变异的中间层,在这一层面当中真正的变异主义一直在高歌舞蹈:在那部分情景中,社会认同产生,语言变体和言语行为相联系。简言之,这部分最终会导致语言变化。在结构主义中,从广义上来讲,这一成果是直接从个体变异到社会共有准则的飞跃。可以肯定地说,反对这种趋势的人都会认同这样的说法,即研究使用中的真实语言意味着多变量类型的分析,涉及诸如用户相关变异,依情景而定的变异性和概念动机等方面。致力于阐明和对比社会维度和认知维度的研究自然而然的可以归入到认知社会语言学的范围内。
- 本文的范围和结构
本文对认知社会语言学有一个全面的非排他性的看法。本文的贡献在于举例说明了四个不同且定义明确的领域。本文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基本方面的理论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指语义和语言变异),2)基于使用和基于语料库的语言变异研究,3)文化模型研究, 4)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系统的意识形态研究。让我们来简要说明为什么这些领域值得特别关注。
作为一种基于使用的语言方法,认知语言学对于诸如区域和社会语言变异等社会语言学问题也是开放的。到目前为止,在认知语言学中,语法和词汇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符号化的概念和指称功能上。认知社会语言学旨在将认知范式扩展到涉及语言符号化的区域和社会模式中,而语言符号化本身也将作为一个主题或与概念结构相平行的范例被研究。它强调不同区域和社会群体中语言使用的方式,这些方式有不同的概念,不同的语法和词汇偏好,以及特定内涵的显著性差异,这就为认知语言学研究指明了社会维度的解析方向。作为一种基于使用的研究方法,认知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具有共同的基础即共同的研究点。首先,认知社会语言学并非脱离上下文、语境、主题以及说话人来研究语言形式,相反,它自然而然地将说话人的社会认知功能置于关注的中心。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心理学领域当然已经广泛研究了社会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但这两个学科都没有使用认知语言学的解释框架。然而,认知社会语言学中的一个假设是,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可能有助于“在旧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看法”。
在世界其他中心地区,基于使用的变异研究由鲁汶大学(该大学有大规模语料库和先进的定量技术)和一批学者开展,这些学者的工作围绕由史蒂芬.格里斯(Stefan Th. Gries)和阿纳托尔(Anatol Stefanowitsch)开发的工具进行研究,例如构式连接性分析。
认知社会语言学也必然要研究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化概念联系,正如认知文化模型的概念所阐述的那样,该学科已经由霍兰和奎恩(1987)从认知人类学中发起,他们在语言学方面贡献很多,还有莱考夫(Lakoff/Kouml;vecses),斯威策(Sweetser), 和楷(Kay)也有不少贡献,更进一步的信息可以从帕默尔(1996)那里了解。本文通过关注语言政策的基础模型及其经专家分析后的影响(即语言学家的分析)和民间认知等方面的影响,来进行本次研究。
此外,本文还涵盖了语言与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这些意识形态渗透到引导和支配社会的制度体系当中。在这方面,本书延续了莱考夫(Lakoff)发起的研究,他在接受皮雷斯.德.奥利维拉(Pires de Olivera)(2000:43-44)采访时被问及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存在,他这样回答:“在我的道德政治中,在史蒂文.温特(Steven Winter)关于律法与认知语言学的新书——《林中空地》中,在帕梅拉. 梅根(Pamela Morgan)关于政治演讲的论文中,以及南希.厄本(Nancy Urban)关于商业隐喻用于重构教育的论文中,都有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存在。”后两位研究人员通过新的研究成果也为本书做出了贡献。
正如莱考夫(Lakoff)的回答所证实的那样,他主要通过意识形态研究来鉴定认知社会语言学,但认知社会语言学所包含的远不止于此。本文将主要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领域相结合,因此,它不仅为莱考夫的主张填充了更多实质性内容,而且还大大拓宽了他对认知社会语言学的看法。
现在,这些广泛的视角可以轻易地给人一种印象,即包含在认知社会语言学范围内的所有内容在该范畴当中都具有相同的地位。为了解释情况并非如此,让我们简单地从原型范畴的角度设想认知社会语言学。与其他非经典范畴中的情况一样,某些特征和维度的组合必然更加重要,而其他组合则更为边缘化。在这个特殊情况下,并根据上面所述的考虑因素,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可以大概描述为,a)探索社会起源本身的语言内部或跨语言变异或者将其纳入其他目的的调查中; b)借鉴认知语言学中提出的理论框架和c)通过实施可靠的实证方法来得出结论。最典型的贡献是拥有这种组合的所有特征。在不同程度上不符合后者要求的贡献可能仍然被认为与该范畴有关,但不得不承认它们将比那些结合三种特征的要更加边缘化。
- 各部分和贡献概述
3.1理论方面:语义和语言变异
第一部分从主要理论角度探讨了认知社会语言学的必要性。有人认为,语义和语言内部概念化的社会维度在基于使用的语法模型中是不可忽视的。例如,原型理论在认知语言学中被广泛接受和实施,但陈规定型和规范性仍然是外围和不明确的概念。同样,传统上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研究的许多问题,例如风格转换和代码转换,非常适合于以认知为导向类型的分析。
在“原型,模式固见和语义规范”中,盖拉茨(Dirk Geeraerts)对原型(Eleanor Rosch)和模式固见(Hilary Putnam)的概念进行了比较,特别提到了语言社区中意义的分布。盖拉茨首先辩称,原型理论研究应该抛开同质语言社区的概念。其次,可以看出,与普特南理论相关的语言劳动的分工与指派在逻辑上是独立的。因此,普特南提出的社会语义模型需要扩展。 盖拉茨提出的替代模型涉及三种类型的社会语义:合作语义(雷纳特.巴奇描述的基于原型的意义扩展),权威语义(如普特南关于语言劳动分工的观点),以及冲突和竞争的语义(当语义选择受到隐然的质疑或明确的争辩时)。
在“风格转换和转变风格:社会认知方法中的语言变异”中,吉特.克里斯蒂安森(Gitte Kristiansen)将变异主义和互动主义社会语言学(即相对稳定的说话者相关因素和动态,情境现象)与一系列众所周知的认知语言学概念结合起来,如原型理论和参考点构式,以提供一种风格转换的社会认知解释。本文分析了可能的过程和机制,通过这些过程和机制,说话人会向不同于自己的准则和方式转变, 或者形成其习惯曲目的部分。本文分两个主要步骤进行。第一部分以人类基于口音方言识别的能力为中心,并论证我们对语言和社会范畴的认识是经验性的,并且这些是通过转喻联系而系统性的相关联:语言代表了社会身份。本文的第二部分侧重于更为活跃的能力展示:语言是表达社会认同的工具。
3.2 基于用法的变异研究
认知语言学声称从根本上讲是基于使用的,但它往往更重视理论,而轻视方法。正如盖拉茨(2005)认为的那样,基于使用的语言学不仅必然涉及一种可靠的经验方法(因为它旨在检查实际的,而非引出的语言行为),而且还涉及在实际语言使用中自我表达社会变异的调查,如在大型文本语料库所证明的。
本节包括一系列学者的文章,这些学者都在语言学研究中根据社会语言学的高度经验标准进行定量语料库分析。本文第一部分采用基于语料库的方法和对比不同的方法论方法,通过阐述调查语言变量的复杂性来作为理论上的引导,但其余部分大多是基于大量文本语料使用的实际案例的例子。
由克里斯.海伦(Kris Heylen),约瑟.图蒙斯(Joseacute; Tummers)和德克.盖拉茨(Dirk Geeraerts)撰写的题为“基于语料库的认知语言学中的方法论问题”的章节促进了对认知语言学中方法论创新的持续讨论。作者批判性地回顾了方法论上最先进的句法变异定量案例研究,并探讨了当必须进行方法选择时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本文比较了两所学校,这两所学校都在努力开发基于语料库数据定量分析的认知语言学实证研究方法:史蒂芬.格里斯(Stefan Gries)和阿纳托尔(Anatol Stefanowitsch)采用的结构方法与研究单位定量词汇学和鲁汶大学的变异语言学所开发的方法相比较,其中本文作者也参与了鲁汶大学的研究。
在他们的章节中,“渠道、构式意义:一个结构性案例研究”,阿纳托尔和格里斯基于以往的贡献回应了海伦的批评言论,并提供给读者大量的案例研究来说明在渠道分析中可以将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19271],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以上是毕业论文外文翻译,课题毕业论文、任务书、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
您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 从目的论看儿童文学翻译——以小王子的两个中文译本为例外文翻译资料
- 英语学习中的性别差异分析外文翻译资料
- 化妆品广告中商标名称的的翻译外文翻译资料
- Analysis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Peking Opera Jarg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kopos Theory ——A Case Study of Farewell My Concubine外文翻译资料
- 基于功能对等论下英美影视作品中俚语的翻译–以美剧《犯罪心理》为例外文翻译资料
- 政治讽刺漫画的多模态话语分析外文翻译资料
- 题目:关于毛姆的艺术家心理自由的研究——以《月亮与六便士》为例外文翻译资料
- 从归化和异化角度分析英文电影字幕翻译——以《冰河世纪》为例外文翻译资料
- 字幕翻译之难:以西班牙电影英文字幕中的建议为例外文翻译资料
- 目的论视角下的美国大片片名翻译外文翻译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