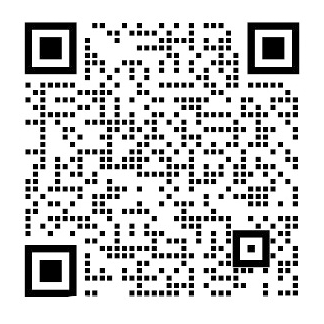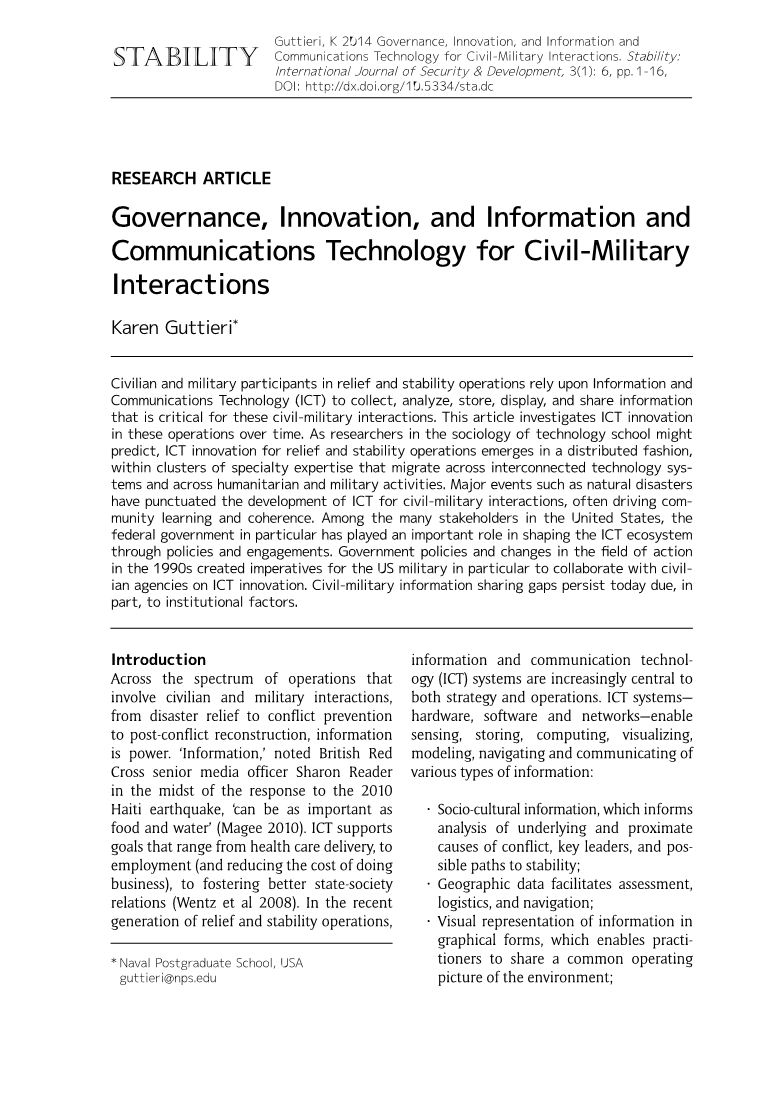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16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军民融合中的治理、创新、信息与通信技术
Karen Guttieri
在救济和稳定行动中,军民两方的参与者依靠信息和通信技术(信息与通讯技术)收集、分析、储存、显示和分享对这些军民互动至关重要的信息。本文将探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操作中的信息与通讯技术创新。正如技术社会学学派的研究人员所预测的那样,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新的救济和稳定行动在各个相互关联的技术系统和人道主义与军事活动之间迁移的专业知识集群范围内,以一种分布式的方式出现。诸如自然灾害之类的重大事件加剧了信息与通信技术在军民相互作用方面的发展,往往会促进共同体的学习和一致性。在美国的众多利益相关者中,尤其是联邦政府,在通过政策和约定塑造信息通讯技术生态系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政府在行动领域的政策和变化为美国军方特别是与民用机构合作开展信息通讯技术革新创造了必要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军民之间的信息共享差距仍然存在,部分原因在于制度因素。
引言
在涉及军民相互作用的各种行动中,从救灾到预防冲突再到冲突后重建,信息就是力量。在2010年海地地震的回应中,英国红十字会资深媒体官员莎伦·朗德(Sharon Reader)指出,“信息可以和食物和水一样重要”(Magee 2010)。信息通信技术支持从提供医疗保健到就业(以及降低商业成本)等目标,以促进更好的国家社会关系(Wentz et al 2008)。在最近一代的救灾和稳定行动中,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系统越来越成为战略和运作的中心。信息与通信技术系统包括硬件、软件和网络使人们能够感知、存储、计算、可视化、建模、导航和交流各种信息:
- 社会文化信息提供了对冲突、关键领导人和可能的稳定途径的根本原因和近因的分析;
- 地理数据便于评估、物流和导航;
- 以图形形式显示信息,使从业人员能够共享环境的共同操作画面;
新的或改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系统使信息共享成为可能,这对目前在预防和应对自然和人为灾害的许多民用和军用机构的协调和解构至关重要。这些系统的组件包括笔记本电脑、个人数字助理(PDA),通信无线电、手机和蜂窝网络(包括WiFi访问互联网和电话服务),互联网或电话服务的卫星系统,全球定位系统(GPS)接收器,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其他映射工具,通过或不通过电线连接的协作软件,视频会议以及通过互联网和其他互联网协议(IP)网络、网站和门户网站的网络电话(VoIP)。现在可以从若干公司和非政府组织(NGO)获得用于商业卫星通信和关键因特网或信息服务的可部署信息与通信技术包(Wentz 2006)。联合国(UN)机构管理他们自己的信息网络,就像正式的军事联盟一样。信息通信技术无处不在,而且“民主化”,在这方面,军民两方人员都有可能使用这些技术(Mancini 2013)。
直到最近,关于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新的讨论都集中在政府的专有技术上,这些技术通常是在保密协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产生了商业化的技术。近年来,这种观点已经越来越陈旧。 许多曾经专属于军事和其他政府机构的技术,如卫星图像和地理定位,现在已经广泛应用(Jones 2002)。此外,国家采购政策的变化已经将这些领域的许多创新转移到民用部门。这一“开放创新”时代的技术能力、供应和治理的含义包括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后果。
在接下来的几节中,我将信息和通信技术创新作为一种由政府的官方行动以及“科技志愿者”团体与国家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社会建设来对待。在复杂的救济和稳定行动的生态系统中,军事行动者,政府官员,国际机构,私营企业和包括这个自愿技术团体在内的非营利组织共享想法,工件和应用程序; 这些努力共同为技术标准的最终协议提供了原材料。尽管这个团体中的许多成员在不区分危机的各种起源(例如战争与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这样做,他们也倾向于通过采取行动来应对危机。简言之,信息和通信技术创新对于复杂业务的创新是分布在互联系统和活动领域的创新之一。诸如自然灾害之类的重大事件促使着这以业务的发生,并且经常强调共同体学习和一致性的演变。最后,联邦政府的国家行动者如今正在努力应对日益扩大和变化的经营环境。美国军事民政方针对民用信息管理寻求一种与民用领域波动的隔绝和开放之间的平衡。总之,他们的目标是抓住信息通信技术提供的机会,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危害。
创新
以往的创新研究与理解救济和稳定操作的出现、信息通信技术的创新以及国家在其中的特殊作用有关。学术文献通常将创新描述为“特定的个人或其他单位所认为的新的观念、实践或对象”(Rogers 2003)。但是,创新研究的弧线已经广泛地从一种流行的专注于发明或“新到世界”的观点转变为一种新颖的、有影响力的创新观点。目前的创新研究发现,除了发明像QWERTY键盘或公制系统这样的新产品之外,创新还涉及到一个被广泛采用的社会过程,从而在该过程中产生各种影响。这种观点已经发展到许多学科和政策领域。
在20世纪80年代,来自多个学科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对大型和相互依赖的系统的创新感兴趣。传统上,学术文献将技术描述为变化的外生驱动因素。相比之下,“技术社会学”学派将技术形式本身描述为社会过程的结果。这些学者强调了制度、政治和文化因素有助于决定技术形态,不仅引起了对“扩散”的关注,还引起了对由“扩散”发生的更广泛的机制的关注。例如,在1880年至1930年之间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比较全国电气化研究中,Thomas Hughes (1983)拓宽了技术历史的视角,在更广泛的过程中研究了大型分布式技术系统的发展过程。Hughes将技术看作是由两个工件(包括他的案例、发电机、继电器和灯)和社会结构(现有技术和行动者、社会需求和地理分布)组成的系统。Hughes发现,在电网发展中,社会因素比机械或科学因素更重要。电网组件关键架构中国家系统的变化以及工程师培训的国家传统“风格” 解释了“电力”形式的变化。Hughes关注不断变化的“系统构建者”的工作,他们在五个时刻为大规模的技术系统提供动力、专业知识和跨越,这些大规模技术系统的特征包括:发明、研发、创新、技术转让和商业化。
创新研究人员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创新如何在组织内部和跨组织之间传播(Lundblad 2003)。创新是一个社会过程;在许多情况下,高度网络化的个体在扩散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Hajek et al 2011)。用户开发减少系统间摩擦的标准(Constant 1980)。在实验过程中,用户注意到差异,并在政策和实际行动形成新的共识。通过这种方式,“广泛的参与者达成了一项当地可强制执行的协议,即某些社会/技术关系是适当和可行的” (Law,2012:127)。
技术创新的三种思考模式是以所要解释的内容为中心(Constant II 1987)。第一种是一个实践模型的共同体,对于解释技术的发展和革命很有用。在这个模型中,明确定义的共同体通常由来自不同学科培训的参与者组成,他们关注功能性失败。第二种模式侧重于组织,为创业、经济和组织增长提供经济和官僚的必要条件。第三种模型以一个系统的视角,包含了另外两种模型,是为了了解大规模社会技术系统的发展。这种系统方法提供了一种广泛的创新视野,使得重新参与的更为广泛的社会动力和力量超越了技术的近期发展。
Langdon Winner(1980,1993)在评论中指出,许多技术进步都是由特权社会群体的需求引起的。 Winner告诫不要忽视政治,政治是技术创新研究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信息通信技术创新在稳定行动中的社会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变化,特别是美国(和全球) 重新定义了在这些任务中民方和军方角色的稳定行动和和平重建模式的变化而变化。
信息通信技术创新与国家
Daniel Breznitz(2007)对信息技术(IT)行业的比较研究表明,国家塑造创新。具体来说,通常需要国家权力来解决高额、高风险的工业研发中市场失灵的问题。Breznitz认为,国家还发挥了促进创新过程本身“固有的集体”性质的作用:“创新在本质上是迭代和合作的”。“因此,在促进、加强和维持创新活动方面,公众行为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07:191)。在信息和通信技术创新对救济和稳定行动的众多贡献者中,美国政府由于它的存在和其巨大的市场支配力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信息通讯技术发展的最初时期开始,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行动就认识到其在和平与战争方面的先进系统的优势。为了说明,1995年,美国外交官选择了俄亥俄州代顿的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作为与缔约方结束波斯尼亚战争的谈判地点。在“任天堂”(Nintendo)的房间里,美国人展示了一个实时的、有争议领土的三维地图。他们试图用图形化的方式表示“对于如今的很多人来说,全部的信息意味着全部的权利”(Gray 1997: 19)。当时,美国军方主导了信息技术领域,部分归功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对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和学术研究的投资,以及与领先企业和研发能力的紧密联系。
几十年来,美国政府内部支持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与军事应用有关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标志着美国的国家角色在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及其在该领域的应用方面的重大转变。
从政府向私营部门“分拆”和从私营部门向政府“自旋”,美国联邦政府在信息通信技术创新方面的角色在功能上和规范上都发生了转变(Guttieri 2000)。不久之后,五角大楼作为这一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政府行为者,开创了一种稳定行动的新概念。它强调稳定行动需要军民协作,其定义是“维持或重建一个安全、可靠的环境,提供必要的政府服务,应急基础设施重建和人道主义救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2009年美国国防政策)。今天,信息技术生态系统中有更多的相关参与者,部分原因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的政策变化。下面描述的这些变化改变了发明、研发、创新、技术转让和商业化的轨迹和形式,包括这种分工的联系和形式。
“分拆”到“自旋”
美国国防部的需求几乎是所有行业军事采购的主要驱动力。许多学者追溯了联邦商业联系在改变采购规则方面的演变(Leslie 1992)。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花费了大量资源进行秘密的技术创新。随着原子弹的发展,永远与战争相联系的科学成为了“国家的监狱”(Leslie 1992:199)。Dwight D. Eisenhower总统在建立军事、工业和学术/科学合作组织方面发挥了作用,他后来在对“军工综合体”的著名评论警告了美国公众(Melman 1974: 263)。这些也是工业界、学术界和军方之间的社交网络。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海军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Naval Research)等政府机构提供了大量的研究合同。最常被引用的冷战创新是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后来被命名为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ARPA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旨在在主要大学组织在跨学科的材料科学研究工作 (Barber 1975)。建立于1969年的ARPANET是一个由四个计算机节点组成的网络,它构成了互联网关键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国家科学委员会1998:8-6)。冷战时代带来了许多围绕洲际弹道导弹的诸如电子、制导系统、结构工程和制造技术的“科学产物”(Leslie 1992:208)。有某些情况下,高端政府采购资金诱使制造商远离低端、更具竞争力的产品(Noble,2011)。美国政府推动信息技术、机械工程和材料研究的总体影响是商业成功的一个时期,随着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能源部和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从政府研究中“拆分”技术而建立了一批活跃的商业公司。
加利福尼亚州硅谷(Silicon Valley)以及沿着128号公路修建的包括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和麻省理工学院(MIT)的马萨诸塞州奇迹等高科技堡垒是联邦军事资助研究的前“炮带”(Gunbelt)的受益者,这并非巧合。许多研究人员为自己创业,雇佣了以前的学生来管理他们的新实验室,剥离了数十家新公司(Saxenian 1994; Siegel and Markoff 1985; Blank 2008)。总而言之,美国技术创新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国家在民用和军事领域建立联系所起到的作用。许多政府资助的技术发展支持了作战和非作战行动。
美国国防部一直是美国政府最大的研发投资者,2013财年投资约650亿美元,其中不包括能源消费部门(Hourihan 2013:25)。 直接生产并非是国家刺激创新新技术的唯一工具。国家还可以监管行业,或者让企业家进入一个理想的领域。政府干预促进信息通信技术等领域的程度可能不如所选择的干预类型(Evans等,1985)。 政策塑造了创新领域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和政治。
作为一般规则,采购和政府研究很容易受到预算削减的影响 (Plumer 2013)。从历史上看,美国政府对包括信息通信技术在内的各种技术创新的投资,通常与五角大楼的预算一样,都经历了繁荣和萧条。在冷战结束后不久的一个资源不断减少的时代,国防部就如何向前推进做出了两项改变游戏规则的修订。1993年,国防部副部长William J. Perry 召集国防工业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被称为“最后的晚餐”(Deutch 2001)。Perry标志着一个大支出时代的结束,并鼓励防务承包商进行整合,以减少对国防的依赖。1993年至1998年间,许多收购案紧随其后。Perry强调,美国国防部将成为众多民用生产商的客户之一。鼓励供应商不依靠国防合同,而是在他们的系统中寻求民用的申请。研究和开发投资似乎没有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事实上,1997年主要由企业推动的美国研发总支出达到2057亿美元创纪录的新高。20世纪70年代,工业研发从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二增加到90年代后期的近四分之三(国家科学委员会1998)。
Perry的另一个主要政策变化是国防部自己的采购系统。从这一点来看,商业现货购买(CO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3655],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以上是毕业论文外文翻译,课题毕业论文、任务书、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程序设计、图纸设计等资料可联系客服协助查找。